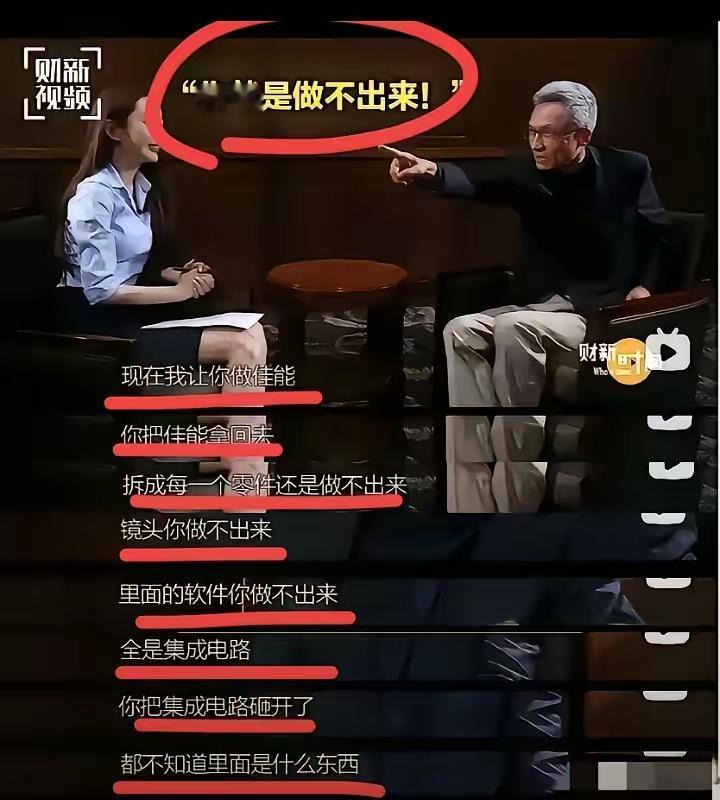我上初三的时候,英语老师是班主任。她那时候还很年轻,没有结婚。每天早晨,她要求我们很早就到校。那时候我们班大半同学住得偏,最远的要坐四十分钟公交,六点刚过就得揣着馒头往车站跑。天不亮的街道没什么人,只有早点摊的灯亮着,我们裹着外套缩着脖子,心里都憋着股怨气,私下里偷偷叫她 “催命鬼”。 初三那年的冬天,天总是亮得特别慢。 我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二十出头,马尾辫甩起来带着刚毕业的冲劲,黑板上的板书永远比晨光先到教室。 她有个铁规矩——六点五十必须坐在座位上早读,迟到一秒钟,就得站着听完早自习。 我们班大半同学住郊区,最远的阿杰要倒两班公交,四十分钟的路,六点刚过就得揣着冷馒头往车站跑。 天不亮的街道像浸在墨水里,只有街角早点摊的灯是暖黄色的,我们裹着校服外套缩着脖子,呵出的白气刚飘起来就散了,心里那点怨气却越积越厚——私下里,我们早给她起了外号,“催命鬼”。 第一次跟她“正面刚”是阿杰迟到那天。 他冲进教室时七点零二分,额头上全是汗,手里的馒头啃了一半,她正站在讲台边翻备课笔记,头都没抬:“门口站着。” 阿杰梗着脖子:“老师,我六点就出门了,公交坏半路……” 她终于抬头,眼睛很亮,却没什么温度:“坐下。明天起,提前十分钟出门。” 后来我们发现,她好像比我们更早。 有次我五点五十到学校,教学楼的铁门刚开,就看见她抱着一摞作业本往办公室走,校服外套没拉拉链,风把她的围巾吹得飘起来,像只赶路的鸟。 你说,那时候我们怎么就没想想,一个没结婚的年轻老师,为什么非要陪着一群半大孩子,在冬天的黑夜里赶早呢? 真正让我们闭嘴的是期末考前那个早读。 那天我起猛了,六点半就到了教室,刚坐下就听见办公室有动静——是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对,就是初三(二)班,孩子们基础弱,我想每天多补半小时……不用不用,我住学校宿舍,早起不麻烦……” 我们总以为她的严格是“折腾”,却没看见她办公室亮到深夜的灯,没算过她每天比我们多走的那两公里路——她住学校宿舍,离教学楼不过五分钟,却比住四十分钟外的我们到得还早。 她没说过“我是为你们好”这类话,却用每天的晨光替我们铺了路——期末考,我们班英语平均分从年级倒数冲到第三,阿杰的公交卡上,多了好几张她偷偷塞的零钱,说是“公交补贴”。 后来毕业聚会上,阿杰喝多了,抱着她哭:“老师,对不起,我们以前叫你……” 她笑着拍他的背,还是那条围巾,这次围得很整齐:“我知道啊,催命鬼嘛。” 全场都笑了,笑着笑着就有人红了眼眶。 很多年后同学聚会,聊起她,总有人说:“要不是当年她那么催,我大概考不上高中。” 原来年少时的我们,总爱用偏见给别人贴标签,却忘了每个“严格”背后,可能藏着一个人偷偷的、笨拙的托举。 现在想起那个冬天的早晨,早点摊的暖黄灯光还在记忆里亮着,只是不再觉得冷了——因为后来我们才知道,比灯光更暖的,是那个被我们叫“催命鬼”的人,用自己的青春,给我们照亮的那段路。
我上初三的时候,英语老师是班主任。她那时候还很年轻,没有结婚。每天早晨,她要求我
卓君直率
2025-12-27 14:41:11
0
阅读: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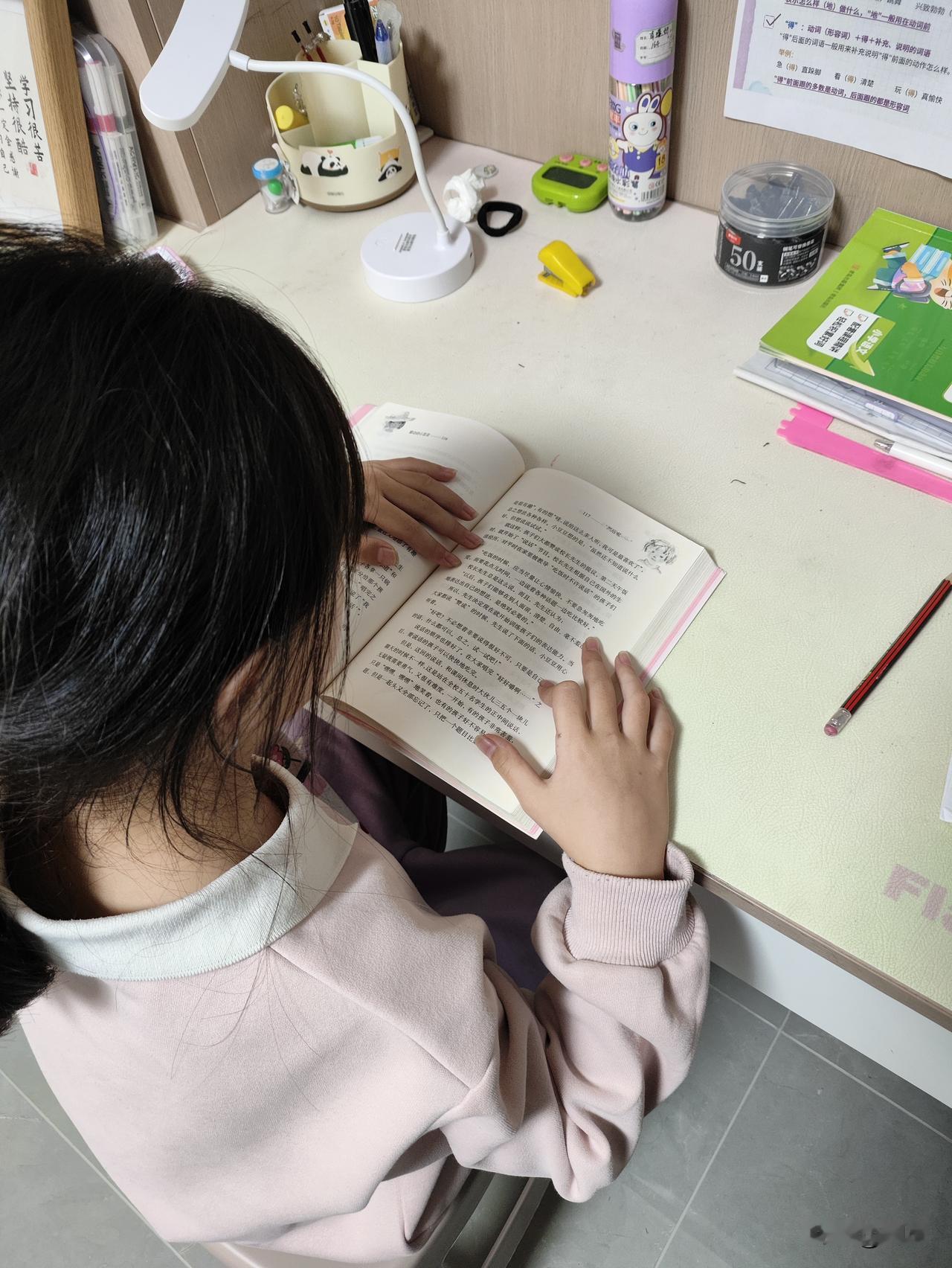





![嗯,考虑一下。。。[思考]](http://image.uczzd.cn/9185228091843325009.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