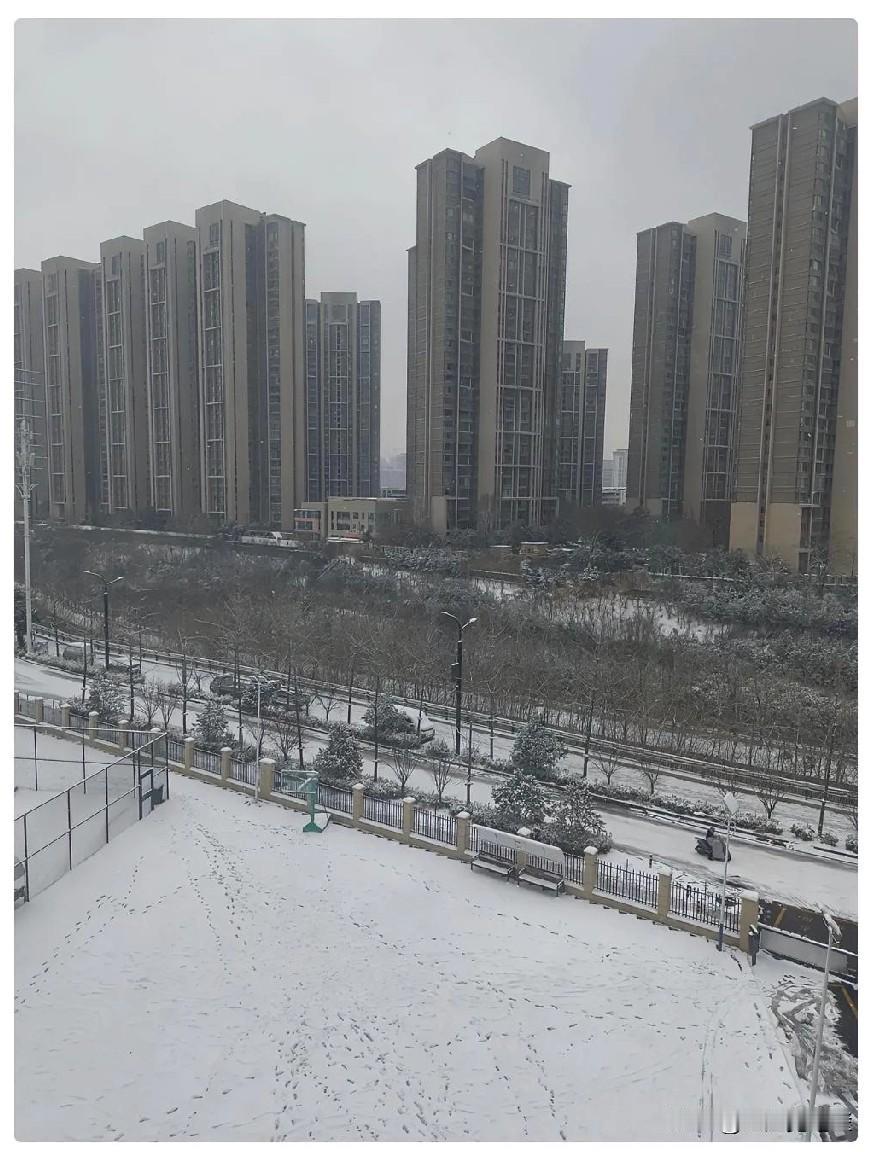1975 年,我把下乡的女知青肚子搞大,她回城后,我以为这事就了了。 那之后,我照样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麻,田里的蚂蚱蹦来蹦去。可心里头总悬着点什么,晚上躺在硬板床上,听着窗根底下蝈蝈叫,瞪着眼到半夜。我娘有回瞅见我发呆,嘟囔说:“魂儿丢啦?”我没吭声,低头扒拉碗里的粥。 大概过了两个月吧,那天晌午,我正在自留地里浇菜。日头毒得很,井水泼在土里嗞嗞冒白气。村会计隔着老远喊我,说公社有我的电话。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们村就大队部有一部电话,平时都是急事才用。我撂下水桶,脚上沾着泥就往大队部跑。 电话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沙,说是她表哥。他说她回城后一直瞒着,后来肚子显了形,家里闹得鸡飞狗跳。她爹把她送到远房亲戚家待产,生了个闺女,但身体垮了,一直低烧。她表哥说:“她不让告诉你,是我偷看了她日记。她眼下在县医院,嘴里老含糊念你们村的名字。你要还有半点良心,就来一趟吧。” 我挂了电话,耳朵里嗡嗡响。墙上贴的旧报纸哗啦哗啦被风吹动一角。我回家把攒的二十块钱和几张粮票全揣上,跟我爹说去县城买农具。走到村口,赶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尘土扬起来,迷得人睁不开眼。 县医院走廊里一股子消毒水味儿。我找到病房,从门缝看见她躺在靠窗的床上,瘦得脱了形,眼睛望着天花板。我站了好一会儿,才推门进去。她看见我,愣了下,然后扯出个很淡的笑,说:“你怎么来了。”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床头柜上放着个搪瓷缸子,里头半杯水早就凉了。 我说,我都知道了。她摇摇头,说孩子送人了,一户好人家,在省城。她说:“你别惦记,都安排好了。”我们沉默了很久,窗外有棵老榆树,知了叫得撕心裂肺。临走,我把钱和粮票塞在她枕头底下,她手指动了动,没拒绝。我说:“你好好的。”她闭上眼,嗯了一声。 我坐最晚一班车回村。路上黑漆漆的,只有车灯照亮前面一小段坑洼的土路。后来,我再没她的消息。只是每年夏天,听到知了叫的时候,会愣一会儿神。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地种,一茬一茬地收,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
姚爸的哥哥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让田静听得心里很不舒服,大伯是这样说的。其实事情起因很
【4评论】【3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