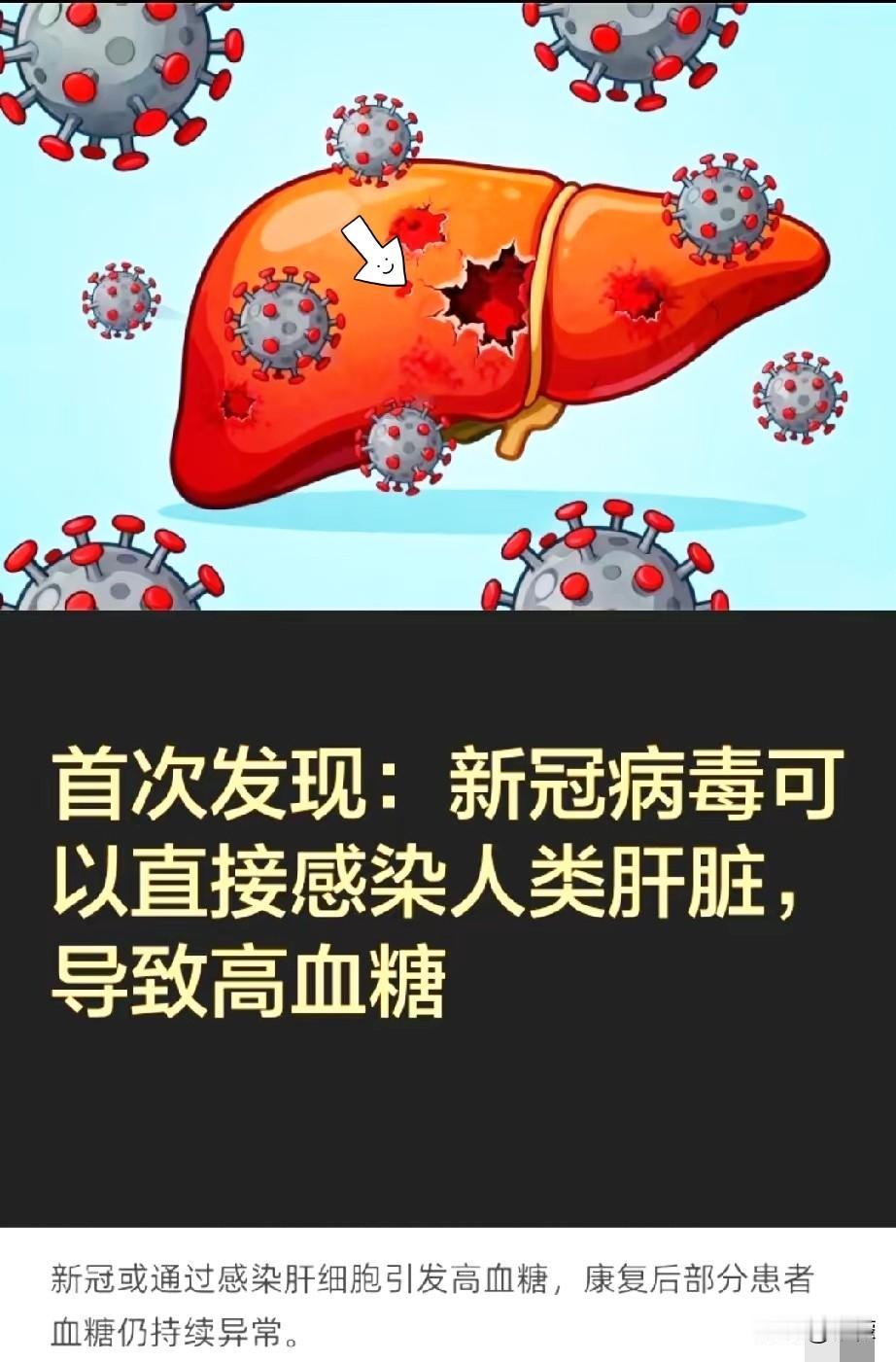“上甘岭战役”伤员救治所里,一个遍体鳞伤的排长因尿不出来尿,憋得脸色通红,一直呻吟,万般无奈下,年仅16岁小姑娘 王清珍 做出的举动,让人震惊而且感动。 这是2026年的1月,距离那个充满硝烟的年份已经过去了七十多载。当我们坐在恒温的房间里回望1952年的上甘岭,视线往往容易被宏大的炮火覆盖。 但如果把焦距拉近,穿透那些岩石和冻土,你会发现那场战役的残酷底色,其实聚焦在一个随时可能炸裂的生体器官上。 那是一个几平米的坑道,即使在今天,我们也难以想象那种窒息感。 空气里没有多少氧气,充斥着硝烟、腐败的脓血味和排泄物的腥臭。就在这口“活棺材”里,躺着排长曹某。他的腹部中弹,膀胱因为尿潴留鼓胀得像个随时会爆的气球。 这里没有战术博弈,只有最原始的生理算术。导尿管被脓血死死堵住,没有负压吸引器,没有注射器。如果不把尿排出来,尿液就会倒灌入腹腔,引发尿毒症。 死亡的倒计时,甚至比外面的炮弹更精准。 站在他身边的,是年仅16岁的卫生员王清珍。在这之前,她是个连甚至都没长全的小姑娘。但在这之后,她成了那个地狱里的“人形负压机”。 现场唯一的工具是一根剪短的洗胃管和几个破塑料瓶。周围有人低声提了一句“用嘴吸”,声音不大,却像重锤砸在人心上。 这是一个极度违背生理本能和世俗伦理的建议,但在那个当下,它是唯一的解法。 王清珍跪下了。她没有时间去权衡少女的羞耻心,那一刻,她面对的是战友因剧痛而抽搐的手指。管子的一头连着死亡,另一头连着她的口腔。 第一口,没反应。第二口,一股温热的、混合着腥臭脓液和尿液的流体冲进了嘴里。 生理性的反胃让她剧烈干呕,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这时候如果是拍电影,镜头可能会切换,但现实没有剪辑。她强行咽下了那股恶心,排空肺部的空气,发起了第三次全力的抽吸。 那一瞬间,堵塞物通了。混着血丝的尿液像泄洪一样喷涌而出,排长紧绷的身体终于松弛下来,生命体征平稳了。 坑道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欢呼。在这种极端的生存环境下,任何赞美都显得轻浮。所有幸存者看着这个嘴角还挂着污物的16岁姑娘,眼里只有一种超越了性别和阶级的敬畏。 在后来的日子里,王清珍的手成了另一种图腾。因为长时间接触脓血和脏水,她的双手溃烂、冻裂,连袜子都穿了三天没空换。她每天要经手20多个重伤员,那些呕吐物常常直接喷在她怀里。 更让人震撼的一幕发生在特级英雄黄继光的遗体旁。当遗体被抬下来时,已经僵硬得无法穿衣。又是王清珍,整整三天三夜,用温水和自己的体温去热敷这位烈士的尸体。 她是在用少女的温度对抗死亡的僵硬,直到烈士的手臂软化,能够体面地穿上军装入殓。 这种行为,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关于“功勋”的认知博弈。连队最初给她评了三等功,这符合常规护理的逻辑。但当师级领导听完“吸尿”和“暖尸”的细节后,直接拍板提级为二等功。 理由很硬:在战场上,能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的世俗道德底线,不惜一切代价换回战友的尊严与生命,这就是最高的战场伦理。 很多年后,那部著名的电影《上甘岭》家喻户晓,片中女卫生员“王兰”唱着《我的祖国》光鲜亮丽。但现实中的王清珍,却几乎从不看这部电影。 她晚年拒绝了无数镜头的追逐,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冷漠”。对于那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来说,银幕上的光影太轻了。她常说的一句话是:“真要死人时,电影帮不了忙。” 那位被救活的排长后来带着妻子千里迢迢来谢恩,王清珍的反应依然是极简主义的。她没有痛哭流涕地忆往昔,只是淡然地说:“排长活着就好。” 在她看来,那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壮举,只是一次必须完成的任务。就像她晚年在县医院门口摆摊义诊,遇到没钱的孕妇直接掏药箱一样,救人是本能,不是表演。 直到2023年10月,这位老人在湖北孝感离世,殡仪馆前自发赶来了3000人。他们中很多人叫不出她的名字,只知道她是那个“吸过尿的女兵”。 她在生前留下过一张手写的字条,上面只有寥寥数语:“我救人,吸尿,活了。” 还有那句振聋发聩的回应,至今读来仍让人头皮发麻:“你们讲道德,我救命。” 这就是王清珍。她拒绝成为一个被神化的符号,她把血、脓和尿液含在嘴里,只为了守住战友最后一口气。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英雄不需要宏大的叙事,她用一生证明了:在生死的极限处,没有高尚与卑微,只有活下去的渴望。 来源:接过奶奶手中的“灯” 解放军报 | 2026年01月24日 1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