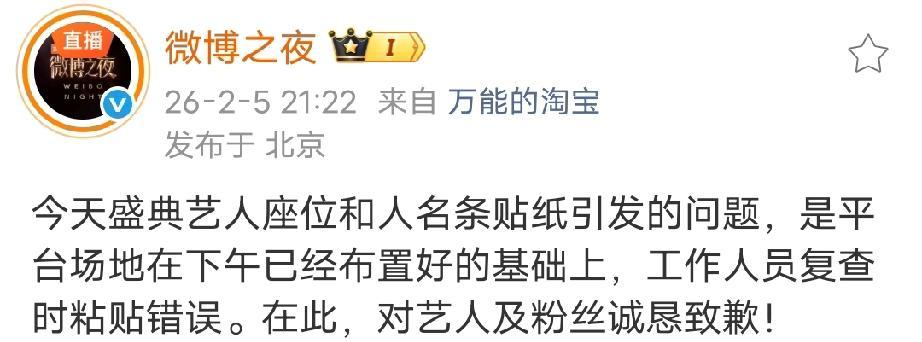1995年,陈忠实《白鹿原》通过茅盾奖初审后,中国作协书记翟泰丰气得怒拍桌子,连连质问:“它有什么好?”两年后,陈忠实凭删减版《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作协书记却气得直拍桌子:实在太遗憾了! 这两声拍桌子的动静,隔了两年,却像一根线串起了《白鹿原》在文坛的跌宕命运。第一声是质疑,第二声是无奈——而中间的曲折,藏着一部作品与现实碰撞的真实温度。 1993年《白鹿原》初版问世时,西安的书店里挤满了人。有个退休教师排了三小时队才买到书,回家连夜读了半本,第二天揣着书跑到陈忠实的办公室,红着眼眶说:“你把我们白鹿原上祖祖辈辈的苦乐都写出来了。”可书里的“直白”也引来了争议:田小娥与黑娃的情欲描写,白嘉轩“腰杆太直”的封建家长形象,在当时的文学评价体系中,都像一根根刺。 1995年茅盾奖初审通过后,翟泰丰的反对声最激烈——他在作协党组会上翻着样书,手指戳着其中几页说:“这书里男女的事写得太露骨,思想倾向也有问题,怎么能评奖?”参会的评委里有朱寨、陈涌这样的老学者,他们力挺《白鹿原》,说“这是中国农村半世纪变迁的史诗”,可争论到最后,还是决定让陈忠实删改后再审。 陈忠实当时在西安灞桥的老房子里,对着样书坐了三天。他抽了四包烟,烟灰落满书桌,最后拿起笔,把田小娥的性描写删了三分之一,把白嘉轩与鹿子霖争斗中“过于尖锐”的句子磨平了棱角。 他跟朋友说:“删改不是认错,是让更多人能看见这本书。”1997年,《白鹿原》(修订版)拿到茅盾奖时,颁奖礼在北京举行,陈忠实穿着母亲织的蓝布衫上台,接过证书时说:“感谢评委给我这个机会,让《白鹿原》能和更多读者见面。”可台下的翟泰丰脸色很难看——他后来在作协内部会上说:“原版里白嘉轩的‘硬’是时代烙印,删了就没了魂,实在太遗憾。” 要理解这两声拍桌子,得回到《白鹿原》的“根”上。陈忠实写这部书用了六年,前三年在白鹿原上跑了上百次,找老农民聊天,记了二十多本笔记。他见过白嘉轩式的族长,在祠堂里敲着惊堂木说“女人要守妇道”;也听过田小娥那样的女人的哭诉,被公公刺死在窑洞里。 他说:“我不是要批判谁,是要把这些活生生的人写出来。”书里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在白鹿原的土地上找到影子——比如白鹿村的“乡约碑”,是陈忠实从村里的老碑上抄下来的;比如黑娃当土匪后回村抢粮,是听他父亲讲过的真事。这样的“真实”,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为“越界”,可恰恰是这种“越界”,让《白鹿原》跳出了“高大全”的文学框架,成了能摸得着温度的作品。 翟泰丰的反对,不是针对陈忠实,是针对“不符合预期”的文学表达。90年代的中国文坛,正经历着从“启蒙”到“多元”的转型,有些老派学者还守着“文以载道”的标准,觉得文学作品要“正面引导”,不能“暴露黑暗”。 可《白鹿原》偏不——它写白嘉轩的“硬”里藏着自私,写鹿子霖的“滑”里透着精明,写黑娃的“野”里混着善良,它把人性的复杂摊在太阳底下,让每个读者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或父辈的影子。这种“不配合”的姿态,让它在获奖路上走了弯路,却也让它活得更久——直到今天,还有年轻人捧着《白鹿原》读,说“原来我们的祖辈是这样活的”。 陈忠实去世前一年,接受采访时说:“我写《白鹿原》,不是为了获奖,是为了给白鹿原留个影。”这句话里没有抱怨,只有释然。他懂翟泰丰的遗憾,也懂自己的坚持——有些作品的价值,不在一时的评价,而在能不能穿过时间的筛子,让后人看见一个时代的真实模样。就像白鹿原上的白鹿,不管有没有人夸它漂亮,它都在那里,踩着自己的影子,一步一步往前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