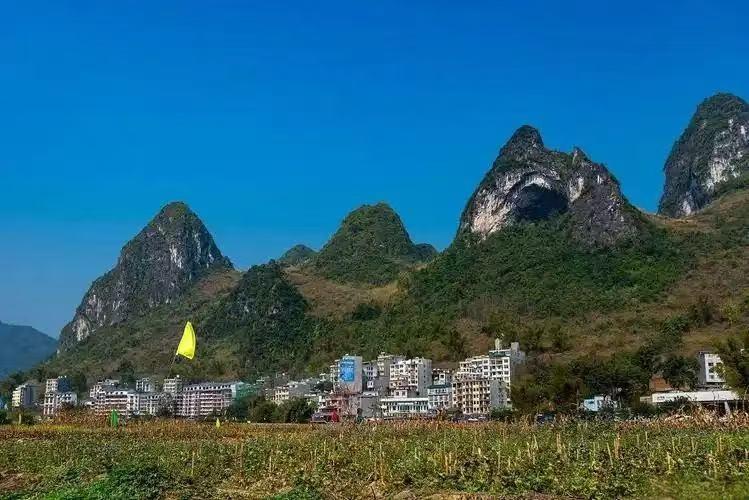1976年3月,广西边防某团王营长的妻子程玲玲,经部队批准,在驻地小镇开了一家小饭馆。说是饭馆,其实也就是给过往之人下碗面条、炒个小菜之类的,仅有几张桌子罢了。时间一长,镇上的人都称她为“玲玲嫂子”。 故事得从1976年的春天说起。那时候,咱们国家还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南疆的广西边防线上,风还很硬。就在那年3月,某边防团王营长的家属程玲玲,拿到了部队的批文,在驻地小镇上开了家小饭馆。这批文,就是她那个年代的“营业执照”,金贵得很。 那个年代,想开个饭馆,最大的难处不是办手续,而是“找东西”。啥都缺,啥都凭票。程玲玲的“进货渠道”,全靠最原始的“人情”和“交换”。后山农户家的孩子上学需要榜样材料,她就用丈夫立功得的奖状去换土豆;河边老李的渔网破了,她帮着补,换来几条小杂鱼;就连供销社的盐,也是她用自己烙的玉米饼换的。 从那天起,“玲玲饭馆”就成了兵哥们的“编外食堂”。巡逻路过的、下哨换防的,都爱往这儿钻。人多没地儿坐,就蹲在门槛上,呼噜呼噜吃得香。程玲玲看着这场景,心里比灶膛的火还暖。 镇上的乡亲们也来。那时候日子紧巴,没人舍得下馆子。也就是赶集的时候,揣着攒了半天的几毛钱,来炒个素菜,就着自带的窝头吃。程玲玲总会多给一勺菜汤,笑着说:“泡着吃,香!” 这勺菜汤里,藏着那个年代最宝贵的东西——体谅。她知道大家伙儿的不易,所以她的饭馆,不只是个买卖,更像个歇脚的暖窝。冬天,手冻裂了口子,她就缝个布套套着继续擀面;夏天,热得像蒸笼,她脸上的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掉。可不管多难,那口热灶从没凉过,那碗面条从没断过。 程玲玲的故事,其实就是当年中国无数个普通人的缩影。她们用最朴素的善良和坚韧,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建立起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微型社会。她拿到的部队批文是“准入许可”,但真正让她立足的,是大家用一碗碗面、一句句“嫂子”给她颁发的“人心许可”。 玲玲嫂子当年面对的是物质的墙,她可以用勤劳和善良去融化它。而今天,李某某他们面对的是一堵数字和规则砌成的墙,坚硬、冰冷,你甚至找不到一个能递上一碗热汤面的人。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悖论。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效率,却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失去了一些温情和包容。 当然,我也不是说现在就人心不古了。恰恰相反,在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那种“玲玲嫂子”式的精神,依然在闪光。 还有个叫孙涵的山东姑娘,硕士毕业后跑到綦江创业,专门做红色研学的项目,带着一波波的大学生和中小学生来寻访“綦迹”。她说,她爷爷就是老红军,她做这件事,感觉是一种很自然的传承。 就像当年的玲玲嫂子,不是在提供一碗果腹的面条,而是在守护一个能温暖人心的精神家园。这种发自内心的守护和传承,比任何商业合同、任何行政命令都来得坚实、滚烫。 时代变了,故事的主角变了,但内核没变。这个内核就是,一个社会,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最终的温度,还是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个社会,不缺“玲玲饭馆”这样的小生意,但可能稀缺的是愿意让“玲玲饭馆”开起来,并用心去呵护它的那种集体善意。我们不能只依赖系统和规则去评判一切,因为最复杂的,永远是人心。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既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也能找回那种街头巷尾的温情。无论是对一个满身疲惫的打工人,还是一个跌倒后想爬起来的“前科人员”,我们都能像当年的兵哥哥和乡亲们对待玲玲嫂子那样,给他一个机会,递上一份善意,说一句:“兄弟,坐,吃碗面。” 因为说到底,一个社会真正的强大,不在于高楼有多高,系统有多快,而在于它的人心,有多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