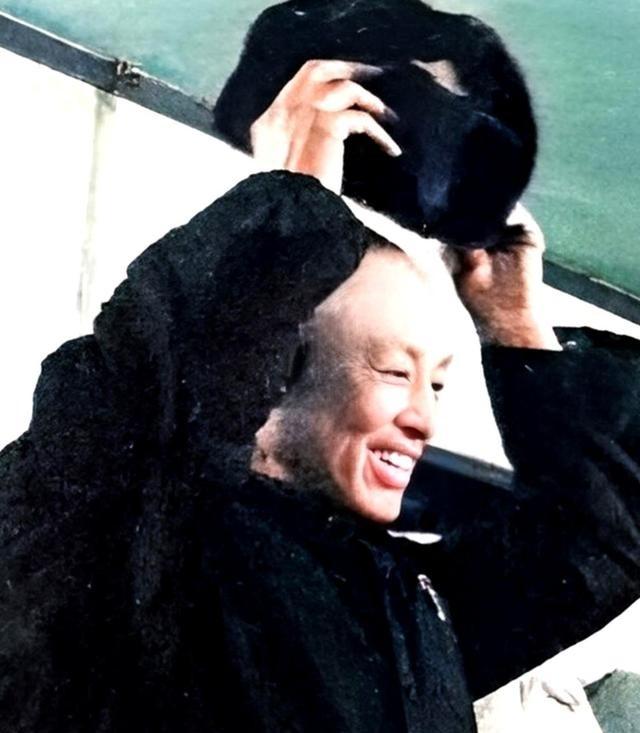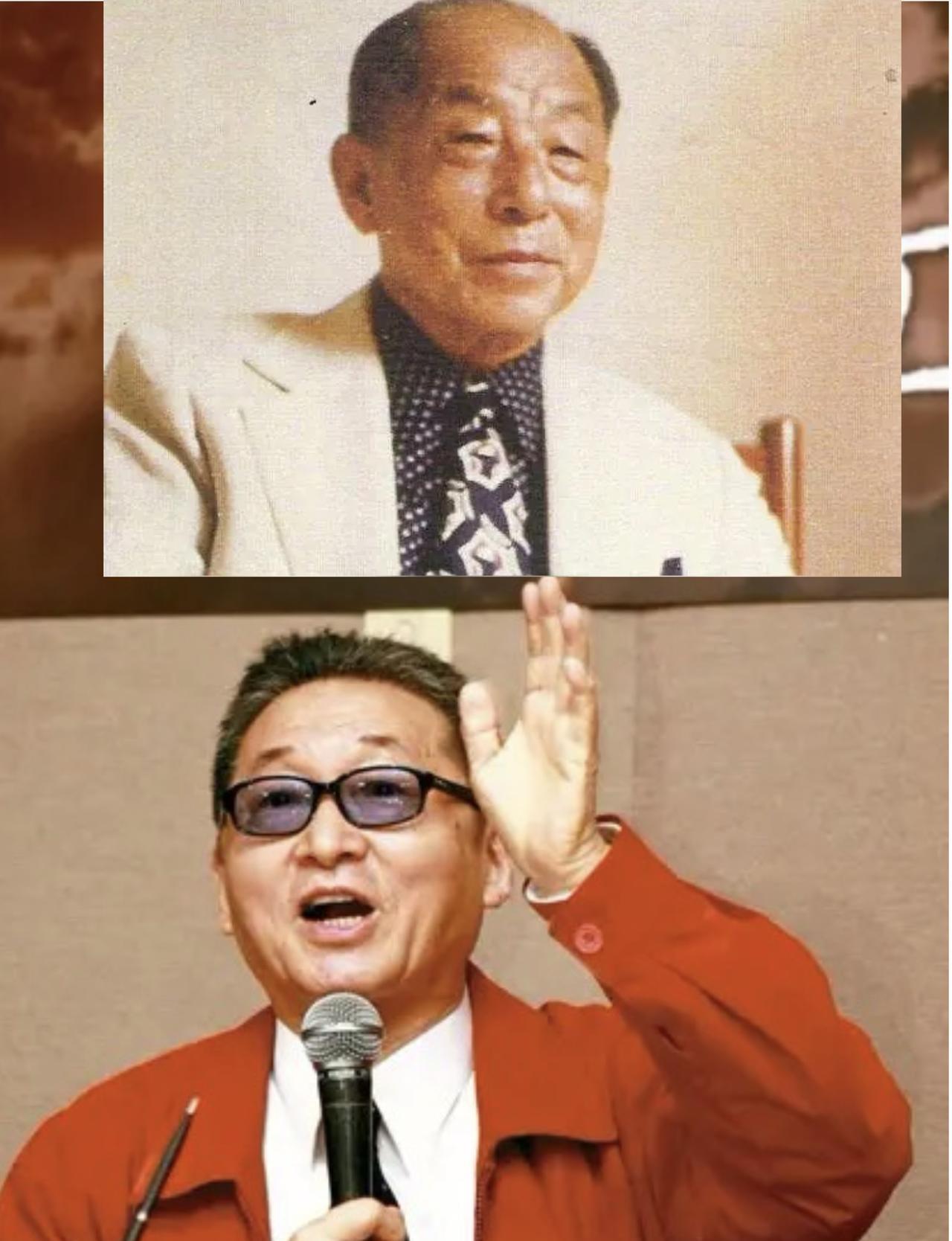1946年, 被老蒋下令“永不录用”的徐恩曾在黄埔江边闲逛, 看到打捞的船只, 突然福至心灵: 既然当不了中统的特务头子, 那就当一个商人吧。 黄埔江的水常年带着股腥味,冬天更冷,江边的风往人身上打,像一层冰膜。 1946年,有人看见徐恩曾站在江边,他穿着风衣,手揣在口袋里,脸色发灰。 那时候,他已经被蒋介石一道手令踢出局,纸上写得干脆:“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从那个位置上掉下来的人,很少再有机会。 他盯着江里拖上来的破木头,嘴角抖了一下,吐出一句话:“当不了头子,那就做商人吧。”谁听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句话像钉子一样钉住了他。 徐恩曾并不是街头混出来的人。 他在上海南洋大学念过书,还去美国留过学,学的是机电工程。 学成回国后,在上海当工程师,按理说可以过一辈子平稳的日子。但1927年形势骤变,陈果夫拉起调查科,他被带进去了。 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 陈果夫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当年是蒋介石的引路人。徐能进这个圈子,不是因为才华过人,而是因为靠上了人。 他在机关里属于那种不显眼的人,不吵不闹,低着头做事。 别人形容他“阴柔”,意思就是没什么硬骨头,但听话、顺从,蒋介石喜欢这种人。 在蒋的眼里,用人得像用狗一样,既要咬人,又要摇尾巴,徐恩曾摇尾巴的功夫比咬人的本事更稳,所以位置一直不低。 1931年出了件大事。 顾顺章在武汉被捕,立刻叛变,准备出卖中共在上海的机关。 武汉那边急电传南京,蔡孟坚为了邀功,把电报不断往总部发。 巧的是,那天晚上徐恩曾不在,他去见情妇了。 中统总部临时由钱壮飞值班。 钱其实是潜伏下来的中共党员,他看见电报,立刻把消息传出去。 于是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在几个小时内紧急撤离,避开了大清洗。 徐恩曾因此留下了污点,可他没被追责,因为他有后台,站得够高。这件事成了他生涯里的一个讽刺:最大的漏洞,却没要了他的命。 三十年代后期,中统逐渐壮大,徐恩曾坐在上头,成了门面。 军统那边的戴笠越来越强,手段狠辣,和美国人合作紧密。 蒋介石需要平衡,就把徐和戴放在两边,互相牵制。南京、上海的小道消息都在说:“这两个‘统’,一天到晚掐架。”他们抢人、抢经费,连情报来源都互相拆。 蒋看得明白,他乐得见他们斗,只要两个势力都不安生,他就能稳住。 徐恩曾性格懒散,不像戴笠那样拼命。他爱女人,常泡在声色场所。 久而久之,中统的名声越来越差。 抗战期间,走私、贪腐的事一桩接一桩。有人利用中统的权力,在中印缅边境搞走私,他的前妻也打着中统的名义倒卖抗战物资。 这些事,很快传到了蒋的耳朵里,戴笠的人更是盯紧了,一点点收集证据。 1945年,一件小事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墙上出现八个字:“总裁独裁,中正不正。”蒋介石看到火冒三丈,下令必须破案。 徐恩曾调动整个系统去查,可查了大半年,毫无结果。 蒋心里对他本就不满,这下更觉得他不中用。 无能加上贪腐,哪怕再顺从,也没法留下,于是那道手令下来,把他彻底踢出局。 2月1日,交接仪式。 那天南京天色阴冷,徐恩曾把印章交出去,没抬头看人,低着头走了。 围观的人窃窃私语,有人冷笑:“完了。”有人叹气:“换谁都差不多。”车子停在门口,他钻进车里,身影一闪就没了。 从那以后,他像被抽空了一样。 1949年春天,他和妻子匆匆逃到台湾。戴笠已经在1946年死了,死在飞机坠落里。 相比之下,徐算活下来了。 在台湾,他没能回到情报系统,转去做生意,日子过得安稳,也平淡,和他年轻时的想象差得远。 社会对他的评价一直分裂。 有人骂他庸才,说他全靠派系撑着,没有真本事,关键时候掉链子。 也有人觉得他至少维系过一个庞大的系统,是蒋的机器里不可缺的齿轮。 其实说白了,他就是那个体制里最普通的一类人。不上不下,既没留下惊人手段,也没做出过硬业绩。 台湾进入冷战年代,情治机构逐渐成型。 那些文件归档、监视手段,追根溯源能找到中统的影子。徐恩曾的经历,像是被切割下来的一部分,被悄悄移植到另一个年代。他自己却再无资格参与。 晚年的他很安静,住在台北一栋普通楼房里。 1980年代,他死在台北,没有波澜。 葬礼简单,也没多少人提起他的名字。 只是偶尔有人说起那句江边的话,带着几分苦笑:“当不了特务头子,那就做商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