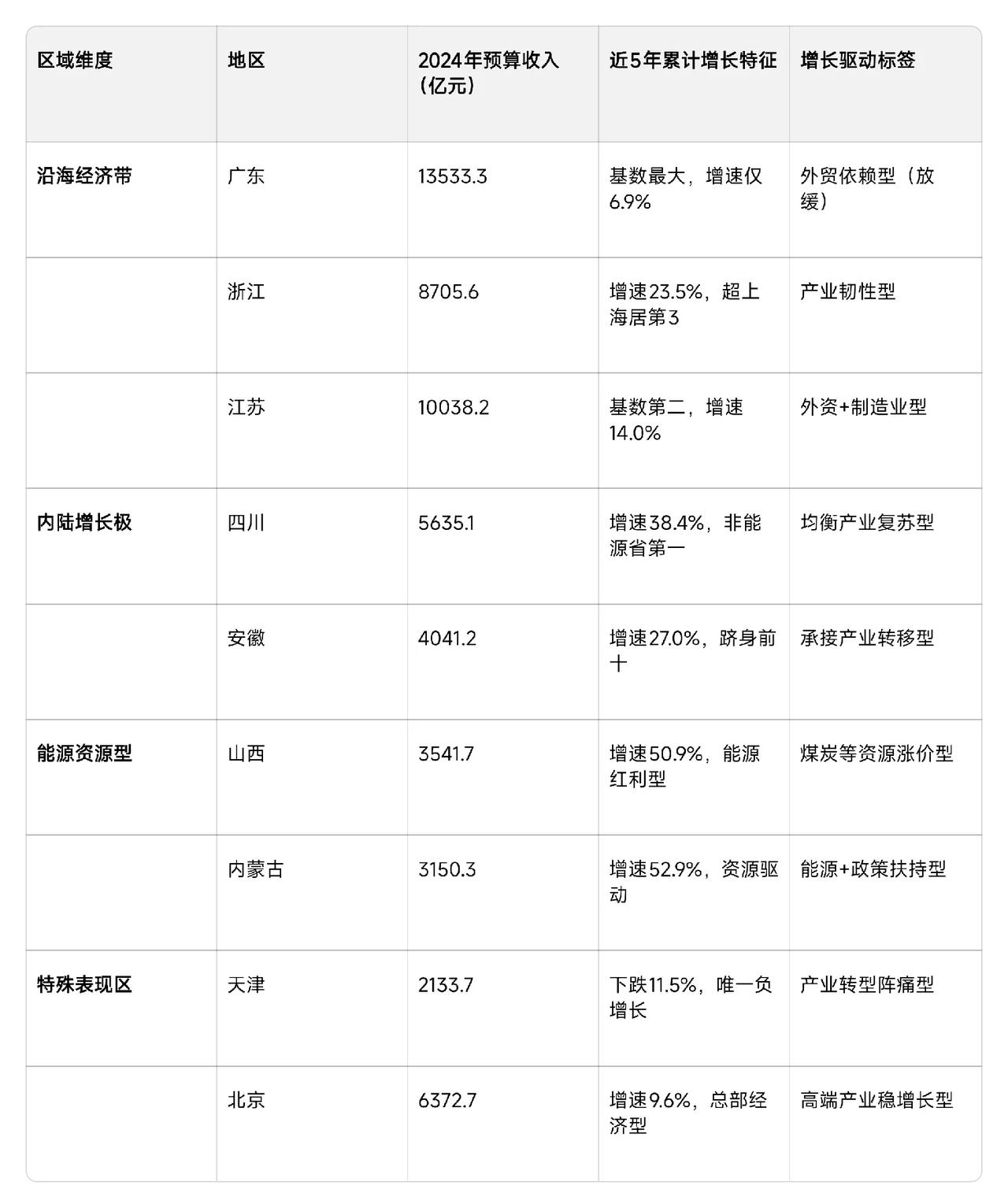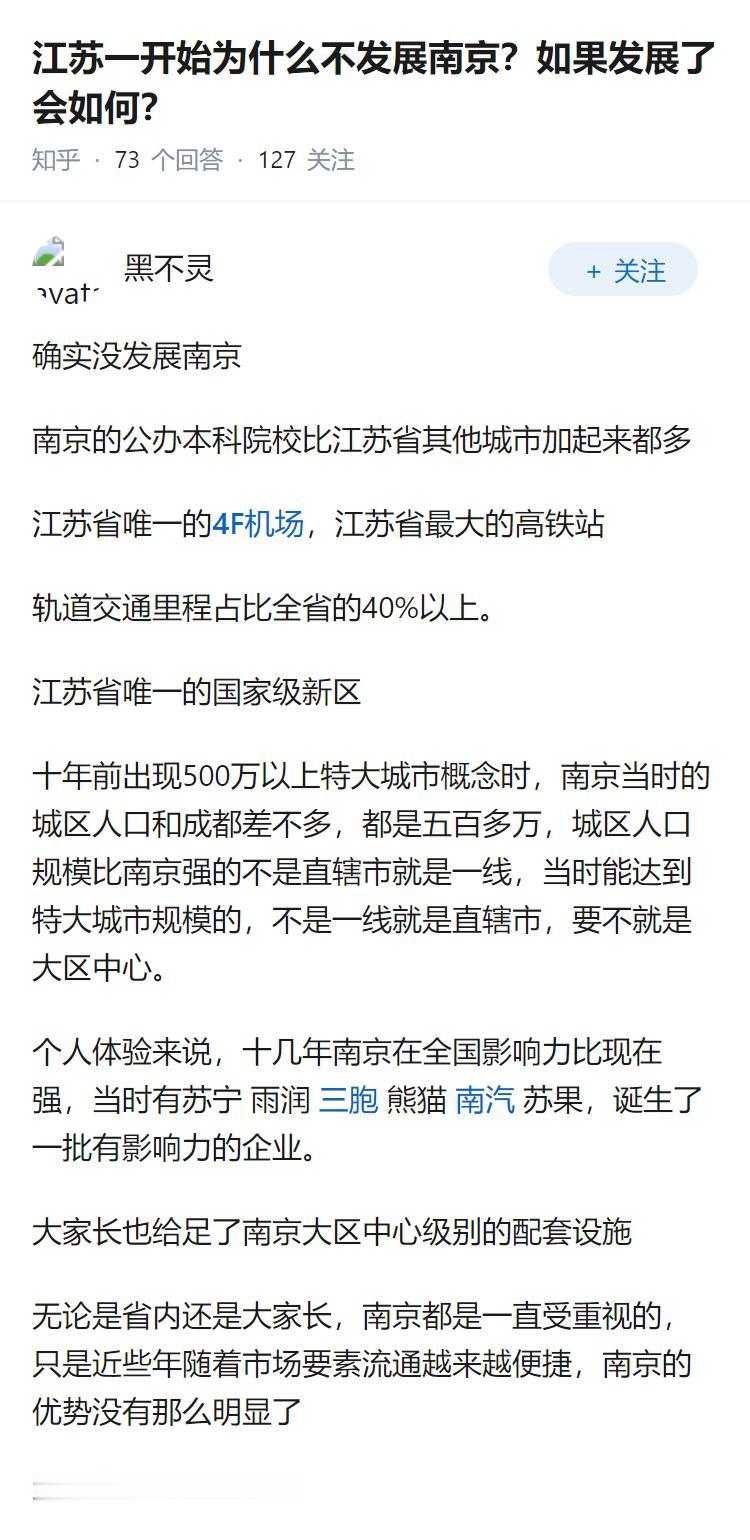苏景华在受审时,用连续三个 “我错了” 开始法庭最后陈述。“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党和组织的培养,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我认罪悔罪……” 这三句重复的忏悔带着颤音,听着像幡然醒悟,可细究起来,每一个字都裹着求生的算计。 去年邻省落马的某厅长,庭审时连说五个 “对不起”,从党和人民说到父母妻儿,最后判决书里果然写了 “认罪态度良好,酌情从轻处罚”。 这种 “忏悔换轻判” 的套路,早被网友编成段子:“认罪三连击,刑期打七折;哭腔加哽咽,再减半年业。” 可苏景华们痛哭流涕时,没提那些被挪用的钱本该花在何处。 审计署 2023 年乡村振兴资金审计报告显示,某省有 3700 万扶贫款被拿去买茅台、送人情,这笔钱按乡村小学建设标准,能盖 18 所带操场的希望小学; 还有地方把危房改造资金挪去修领导 “接待别墅”,导致山区老人冬天仍住在漏风的土坯房里。 那些教室漏雨的窟窿、老人冻裂的手,比他们在法庭上挤出来的眼泪,真实得多,也沉重得多。 有从事纪检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同志说过:“贪官认罪像夏天的雷阵雨,看着声势大,雨点砸在地上,没一会儿就干了,留不下半点痕迹。” 江苏省纪委监委去年通报的案例里,超过 60% 的落马官员在庭审前会突然 “确诊抑郁症”,有的还拿着医院诊断书求同情,可这些人的 “病症”,一到宣判后就奇迹般好转,比精神科医院的治愈率还高。 他们哪是真抑郁,不过是把法庭当成最后的表演舞台,想靠 “弱者人设” 博个轻判。 老百姓早把这套把戏看得透透的。 之前微博上 贪官的眼泪值几个钱 的话题里,点赞量超 50 万的评论是:“他们哭的是丢了的乌纱帽、没花完的赃款,我们疼的是被挪用的养老钱、孩子的教育款。” 中纪委官网公布的 2022 年反腐数据更扎心:当年追回的赃款赃物中,有 34.7% 已经被贪官挥霍一空,有的变成了海外豪宅首付,有的成了子女留学学费,还有的换成了奢侈品店购物袋 。 这些钱里,说不定就有环卫工人扫街攒下的纳税钱,有农民卖粮食换来的补贴款。 为什么总有贪官前赴后继演这出 “忏悔戏”? 心理学里的 “道德许可效应” 能解释 —— 当人反复用语言表达忏悔时,大脑会产生 “已经付出代价” 的错觉,仿佛说几句 “我错了”,就能抵消之前的贪腐行为。 苏景华说那三个 “我错了” 的时候,说不定自己都被那股 “真诚” 骗了,可法律从不是靠眼泪衡量对错的地方,量刑依据里只有贪污数额、犯罪情节、退赃情况,从来没有 “演技评分” 这一项。 不是没有贪官懂 “悔罪” 该怎么来。 重庆去年落马的某区建委主任,被捕时电脑里存着《演员的自我修养》,大概想靠演技蒙混过关,可庭审时却一句话说不出来 。 纪检组直接甩出来他转移赃款的区块链记录,每一笔转账的时间、金额、收款账户,连小数点后两位都清清楚楚,甚至包括他用微信红包给情人发的 5200 元,都被溯源回来。 现在反腐早就不靠 “攻心”,大数据能查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账单,甚至连多年前的购物发票都能调出来,哭得再惨,也抵不过账本上的铁证。 云南去年有个自首的县财政局局长,投案时没带别的,就带了 23 本手写的记账本。 从第一次收 1000 元购物卡,到后来收 50 万元现金,连下属送的一筐土鸡蛋,他都按市场价折算成 800 元记在本子上,最后连本带利退了 127 万元。 这种把 “悔罪” 落在实处的举动,比在法庭上嚎啕大哭、捶胸顿足的 “影帝” 们,强了不止一万倍。 最高检去年的工作报告里说得很明白:是否主动退赃退赔、是否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才是判断认罪悔罪态度的 “硬指标”,光靠嘴说,没用。 苏景华的三个 “我错了”,说到底就是一场没演好的戏。 贪官们该明白,法庭不是舞台,法律不是观众,那些被他们伤害的民生、被他们践踏的信任,不是几句忏悔就能弥补的。 真正的悔罪,不是在庭审时挤出眼泪,而是在犯错前守住底线;不是在落网后求轻判,而是在任上把每一分公款都花在老百姓身上。 这一点,再高明的 “演技”,也装不出来。 信源:苏景华: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鲁中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