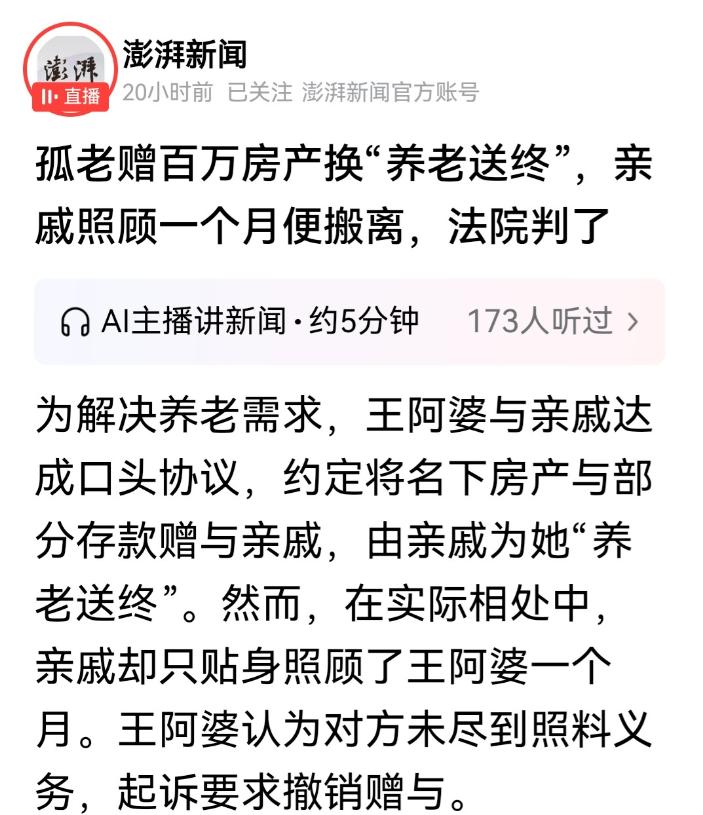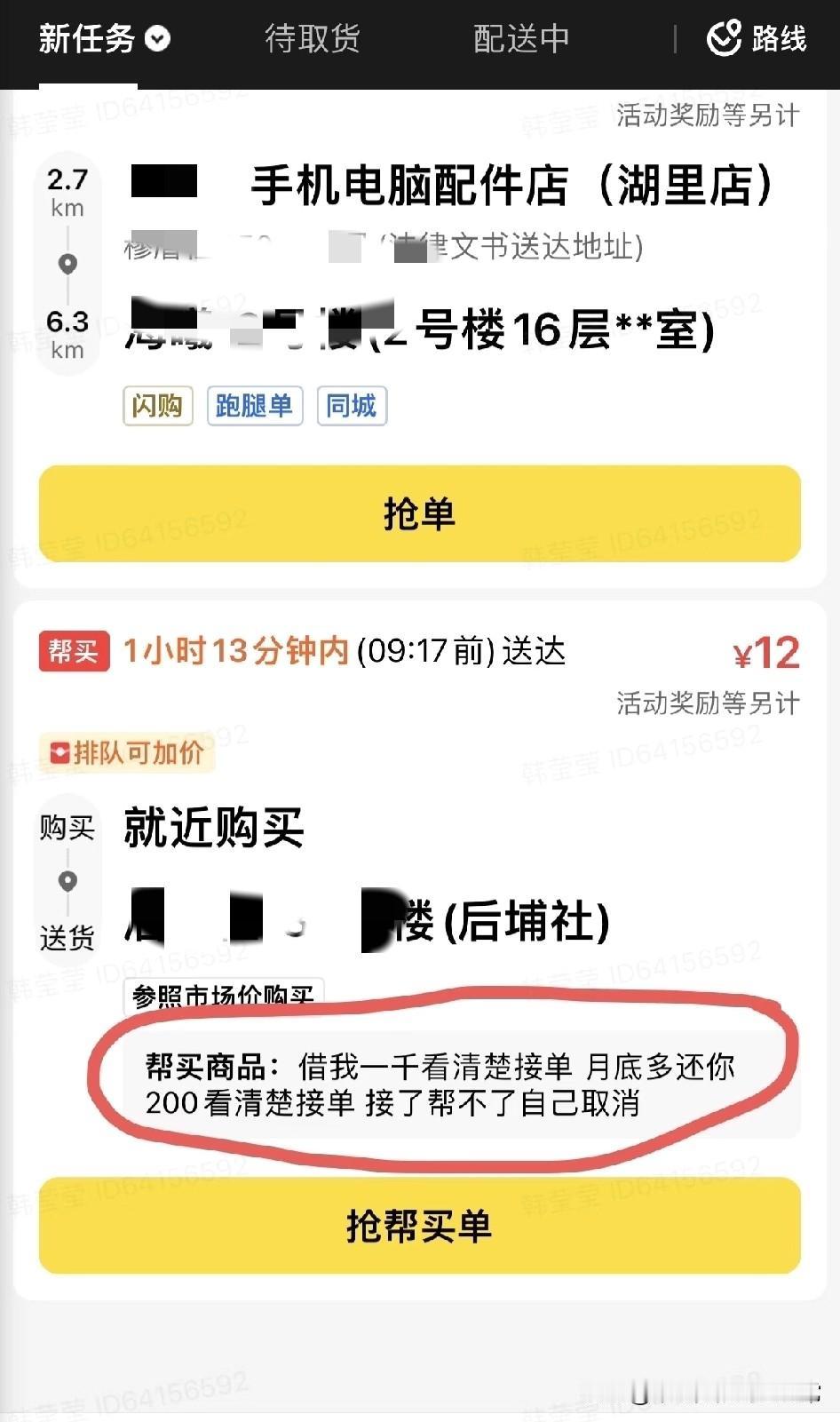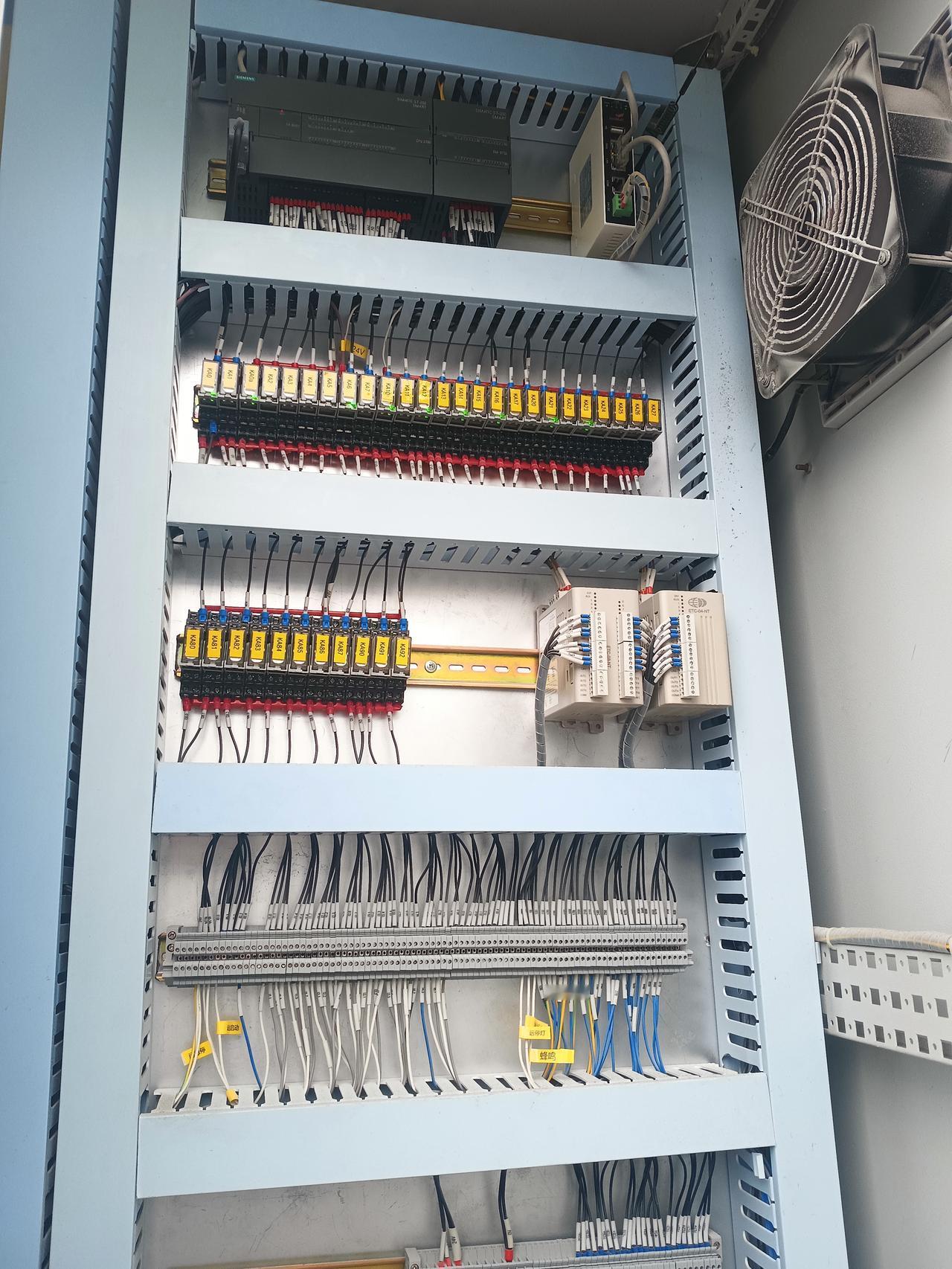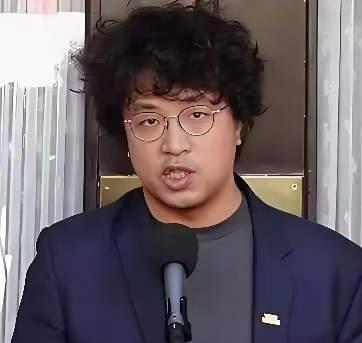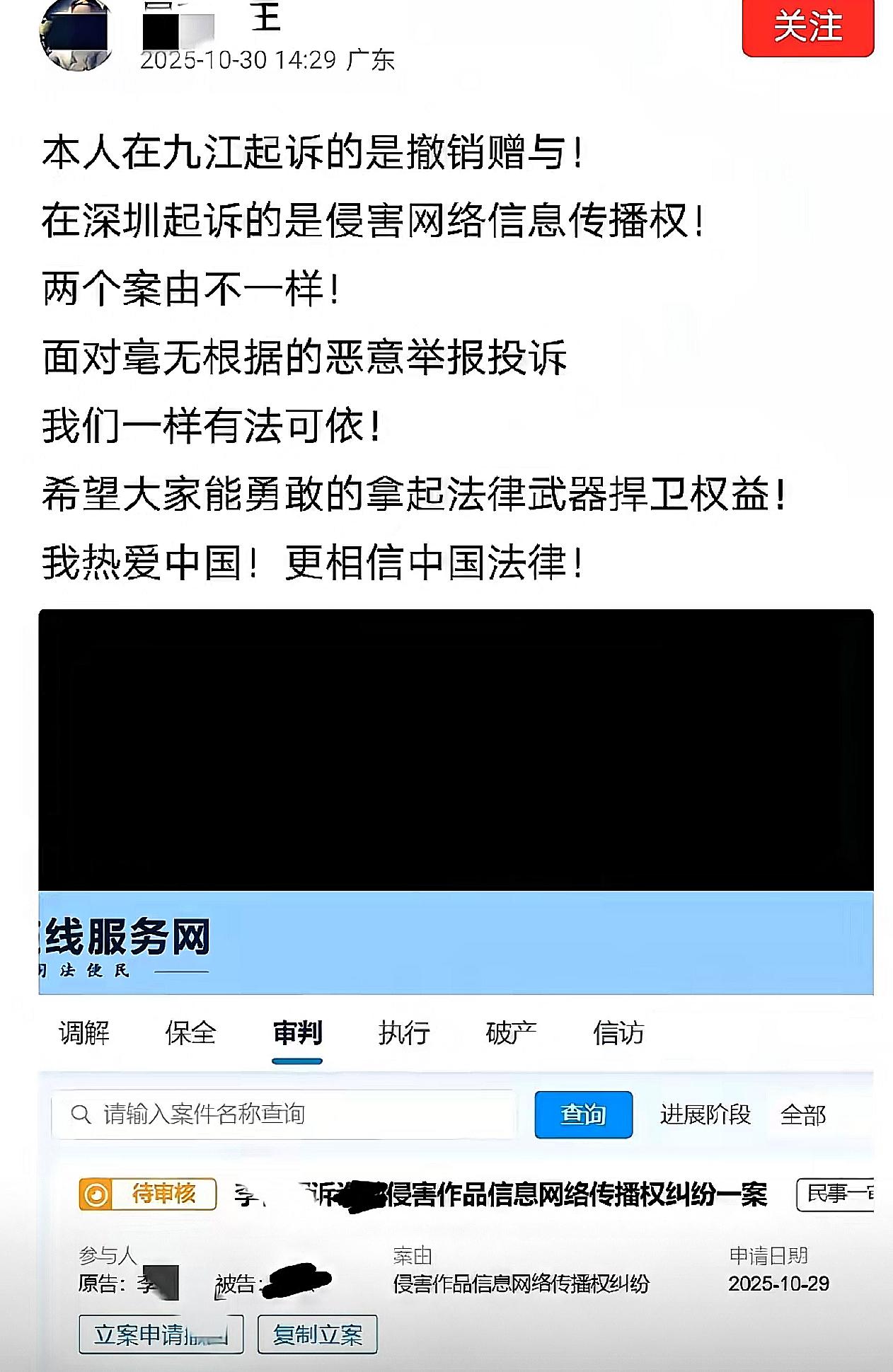上海,王阿婆无儿无女,晚年孤身一人。她希望找一份亲情依托,便将自己价值数百万的房产及42.8万元存款赠与侄女一家,换取“养老送终”的承诺。然而,房产到手后,侄女一家仅同住28天便离开,从此不再照顾。老人无奈起诉,希望收回财产。最后法院判了。 王阿婆年轻时与丈夫恩爱有加,生活富足。唯一的遗憾,是膝下无子女。老伴去世后,她孤独地生活在那套熟悉的房子里,行动渐渐不便。她看着邻居家的老人有儿孙照料,心里常常发怵。她开始担心:“如果哪天我起不来了,连口水都没人端怎么办?” 在多番思虑后,王阿婆想到自己还有一个侄女王女士,是兄长的女儿。两人平日来往不多,但王女士性格爽快,曾主动表示会照顾姑姑。于是,王阿婆决定以房产和存款为“养老保障”,换取侄女的照顾。 2024年4月,双方在家中达成口头协议:王阿婆将房屋过户至侄女的儿子小王名下,并将42.8万元存款转入侄女账户。侄女承诺搬入照顾王阿婆,承担生活起居费用,直至老人去世,并负责料理后事。那一刻,王阿婆觉得自己找到了依靠。 然而,现实很快打破了幻想。王女士一家搬入仅28天,就以“生活习惯不同”为由离开。此后再未照料老人。房产和存款已全部转出,老人却再度陷入孤独。她反复拨打侄女电话无人接听,只能叹气说:“房子没了,钱也没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 在多次沟通无果后,王阿婆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房产与存款。她认为,这笔赠与是附条件的,侄女既然没有履行赡养义务,就应撤销赠与。 侄女王女士在庭上辩称,自己当初出于“善心”照顾姑姑,已经尽力。她解释:“姑姑脾气古怪,怎么做都不满意,我一家人都受委屈。”她同时表示,老人只是希望她帮忙料理后事,并未约定长期赡养。 案件审理中,法院查明事实:王阿婆在赠与前后身体健康、意识清晰,侄女一家确实搬入并照料过,但时间极短。双方虽未形成书面协议,但有邻居证言证明,王阿婆曾公开表示“把房子给侄女一家养老送终”。 法院认为,双方虽为口头约定,但符合《民法典》第657条关于赠与合同的定义——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行为即视为合同成立。此赠与行为同时附有义务,即受赠人须履行“养老送终”责任。 法院指出,侄女一家仅照顾老人28天便离开,明显未履行赡养义务,且赠与目的未实现,构成撤销条件。遂判决撤销赠与,要求返还房产及部分存款。 考虑到侄女在照顾期间确实承担部分生活费用,法院酌情扣除,最终判令返还房产及存款25万元。 一审宣判后,小王提起上诉,辩称赠与仅是为“身后料理后事”,并非长期赡养。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认为此说法与常理不符:“若仅为身后之事,不可能立即过户房产及转账存款。” 二审判决明确指出,王阿婆的赠与属附义务赠与合同。侄女一家既然收受财产,就应履行义务。既未照顾老人,也未履行“生养死葬”,赠与目的落空,依法应撤销。 从法理上看,本案兼具警示与启示意义:首先,附义务赠与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赠与人将财产附条件转让,受赠人应履行义务,否则赠与人有权撤销。《民法典》第663条赋予赠与人撤销权,其时效为自知晓撤销事由起一年内。王阿婆在侄女离开后立即起诉,符合时效规定。 其次,口头协议虽缺乏书面证据,但可通过其他证据补强。法院综合邻居证言、银行转账记录、房产过户时间,确认双方存在“以赡养换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合同有效。 再次,本案体现了公平原则与公序良俗的司法考量。若侄女一家以短期照顾换取数百万财产,明显违背公平。法院判决撤销赠与,是对弱势老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也暴露了现实中的法律盲区:许多老人缺乏法律意识,未签订书面协议或见证文件,容易在纠纷中陷入被动。若王阿婆未能及时维权,可能永远失去财产。 在社会层面,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家庭赡养纠纷,更折射出老龄化社会下的伦理困局。越来越多的老人希望通过“以房养老”换取照料,却忽视了法律程序的重要性。 从王阿婆的角度看,她以信任换安全,却因口头约定失去了依靠。从法院的角度看,判决不仅是对个案的裁决,更是对社会的提醒——法律不能替代亲情,但可以防止亲情被滥用。 如今,王阿婆的房子与存款已依法返还。她说得最平静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怕没钱,我是怕到老了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