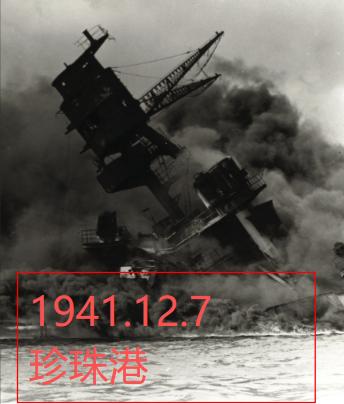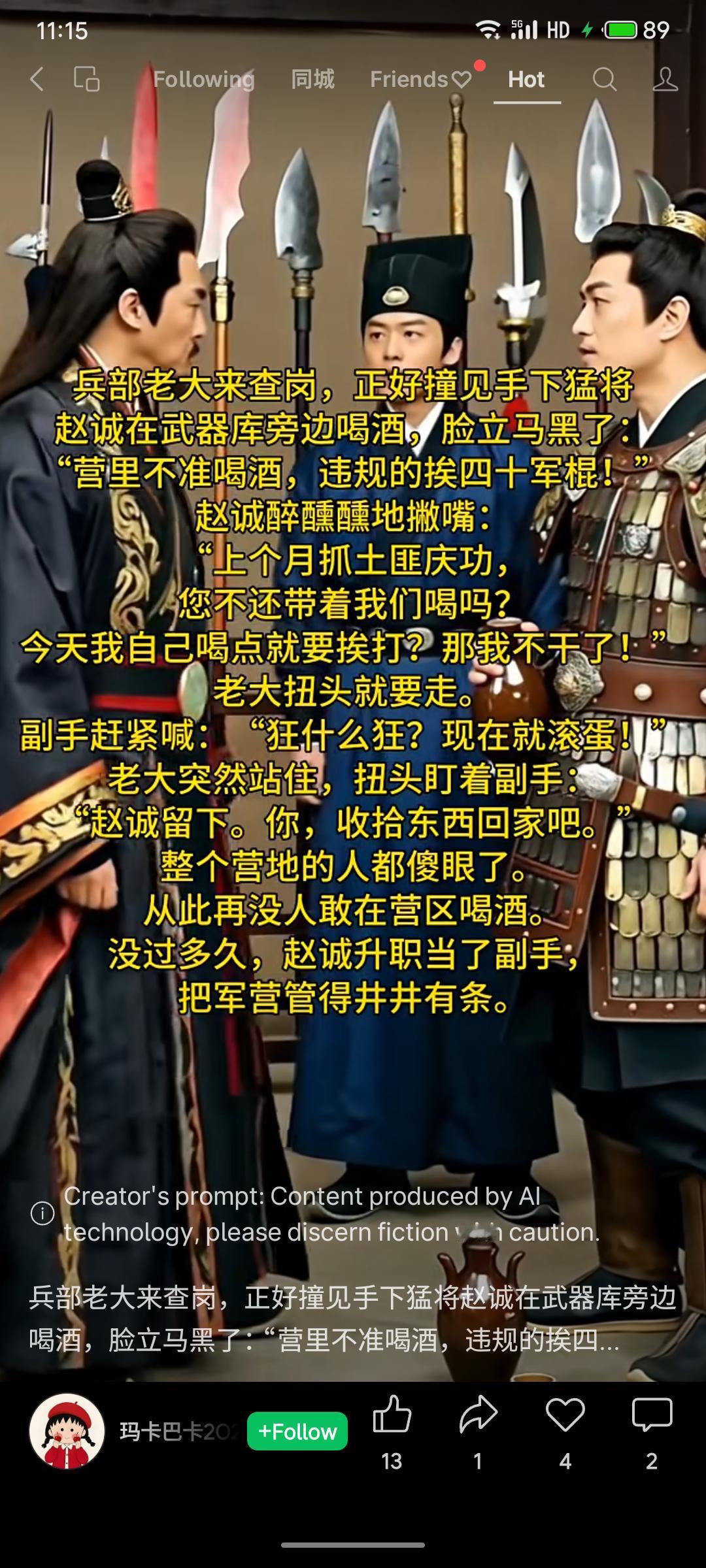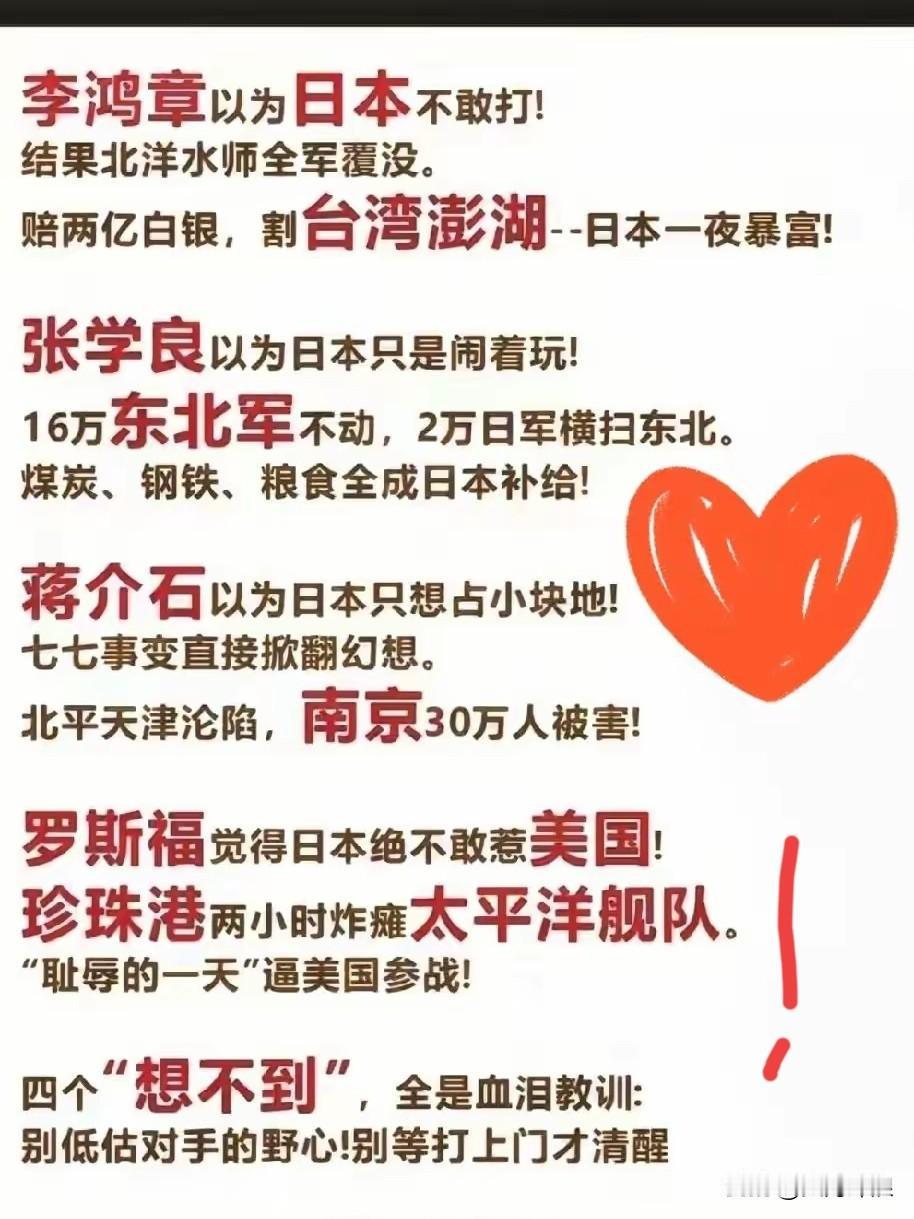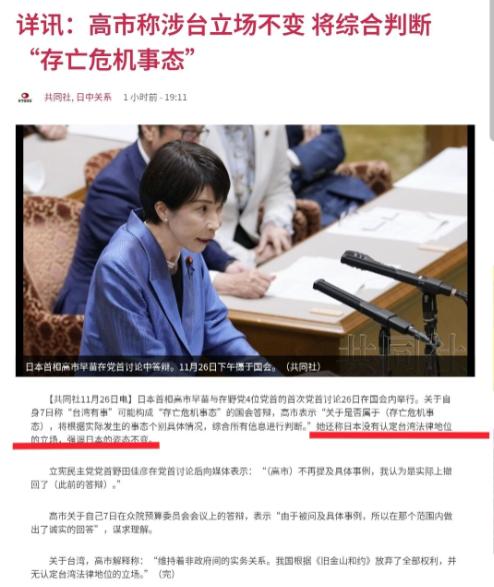司马伦篡位为何会被群起而攻之? 司马伦篡位之所以招致天下共讨,根子上在于他既无驾驭全局的能力,又彻底打破了西晋宗室权力平衡的脆弱框架。 这个司马懿第九子,一生都在证明自己如何不适合坐在权力中枢——早年偷窃侄孙司马炎的御裘,镇守关中时逼反羌氐,投靠贾南风时又亲手导演太子之死,每一步都在积累恶果。 当他踩着张华等忠臣的血登上皇位时,看似完成了从权臣到帝王的跳跃,实则踏入了西晋宗室精心布置的陷阱。 元康十年那场政变,司马伦用伪造的诏书骗开宫门,诛杀贾谧时贾后那句“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道破了他的致命缺陷:永远只抓权力的尾巴。 他以为杀光贾后党羽、罢免满朝文武就能掌权,却不知道张华、裴頠这些被他视为绊脚石的能臣,恰恰是维系西晋官僚体系的梁柱。 当尚书郎师景要求验看皇帝手诏时,他二话不说斩首示众,这种对制度底线的践踏,让士族官僚寒心——他们可以接受权臣,但绝不能容忍一个连表面规矩都不屑维持的莽夫。 篡位后的荒唐操作,彻底暴露了司马伦集团的短视。为了收买人心,他将秀才孝廉免试授官,十六岁太学生直接入仕,郡县小吏全部封侯,以至于“貂不足,狗尾续”成为笑柄。 这种竭泽而渔的封赏,耗尽了西晋的官爵资源,更让真正的功臣寒心——齐王司马冏率军入宫时的血勇,在司马伦眼里不过是与杂役同等的功劳。当三王起兵时,那些被白版封侯的底层官吏,宁可持观望态度,也不愿为这个毫无章法的朝廷卖命。 最致命的误判,在于对宗室诸王的轻视。司马伦以为加封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为开府仪同三司,就能安抚这些手握重兵的藩王。 他不知道,早在诛杀太子时,诸王就已看穿他的野心。成都王司马颖的谋士卢志曾警告:“赵王篡逆,天下忠义之士莫不欲诛之。”当司马伦在洛阳大搞巫祝迷信,让道士假传司马懿神谕时,诸王正在各自封地厉兵秣马——他们等待的不是“清君侧”的借口,而是瓜分权力的时机。 军事上的混乱,加速了崩溃。孙秀派往抵御司马颖的孙会,不过是个卖马小吏的儿子,竟与宿将许超争权,导致黄桥之战先胜后败。 更荒唐的是,当张泓在阳翟大破齐王军时,洛阳城内竟因谣言先庆功后恐慌,这种指挥系统的失灵,让前线将士心寒。 三王联军不过十万,而司马伦坐拥二十万禁军,却因将领互相猜忌,六十天内丧师近半。最讽刺的是,直到兵败前夕,司马伦还在宣帝庙祈祷,以为祖父的阴灵能保佑他的皇位。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司马伦破坏了西晋“宗藩拱卫”的立国根基。自司马炎大封宗室以来,诸王虽有野心,但维系着“共尊皇室”的默契。 贾后乱政时,诸王尚可借“清君侧”名义入朝;但司马伦废黜惠帝自立,等于撕毁了这层契约——叔祖父夺侄孙的皇位,让所有宗室都看到:权力可以靠暴力夺取,而非血缘伦理。 齐王司马冏檄文中“逆臣孙秀,迷误赵王”的措辞,表面声讨孙秀,实则指向整个篡位集团——他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来掩盖各自的野心。 当司马伦饮下毒酒前哭喊“孙秀误我”时,他始终没明白:真正误他的,是对权力本质的无知。西晋的天下,是司马懿父子三代与士族、宗室妥协的结果,不是靠伪造诏书和白版侯爵就能坐稳的。 他杀光了能制衡诸王的忠臣,又用荒唐的封赏得罪了士族,最终让自己成为诸王争霸的第一个靶子。三王起兵时,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的景象,不是因为支持某王,而是渴望结束这个连基本秩序都维持不了的政权。 这场闹剧般的篡位,本质是西晋宗室内斗的总爆发。司马伦不是第一个权臣,却是第一个彻底践踏规则的破坏者。 他的失败,不是因为篡位本身,而是他既没有曹操的权谋,也缺乏司马昭的威慑,却妄想复制司马懿的隐忍。当他在太极殿接受玉玺时,殿外的槐树正在落叶——那不是祥瑞,而是八王之乱的血色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