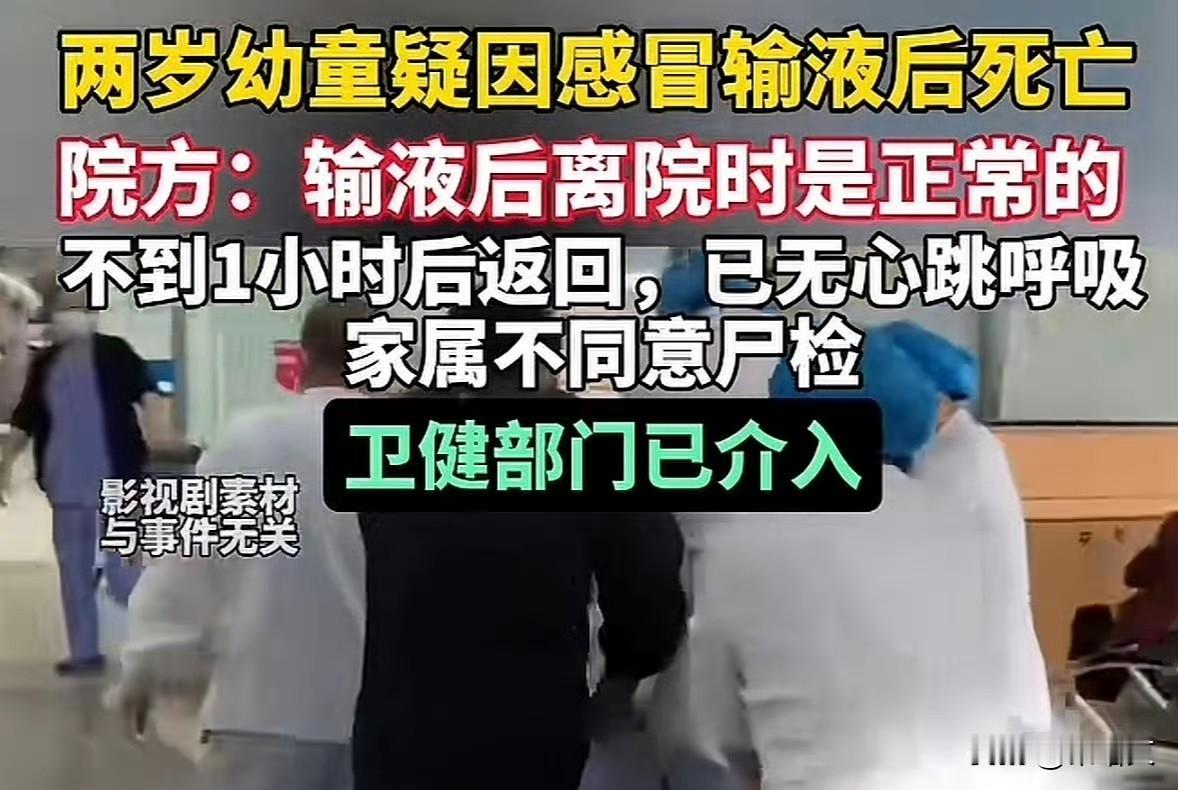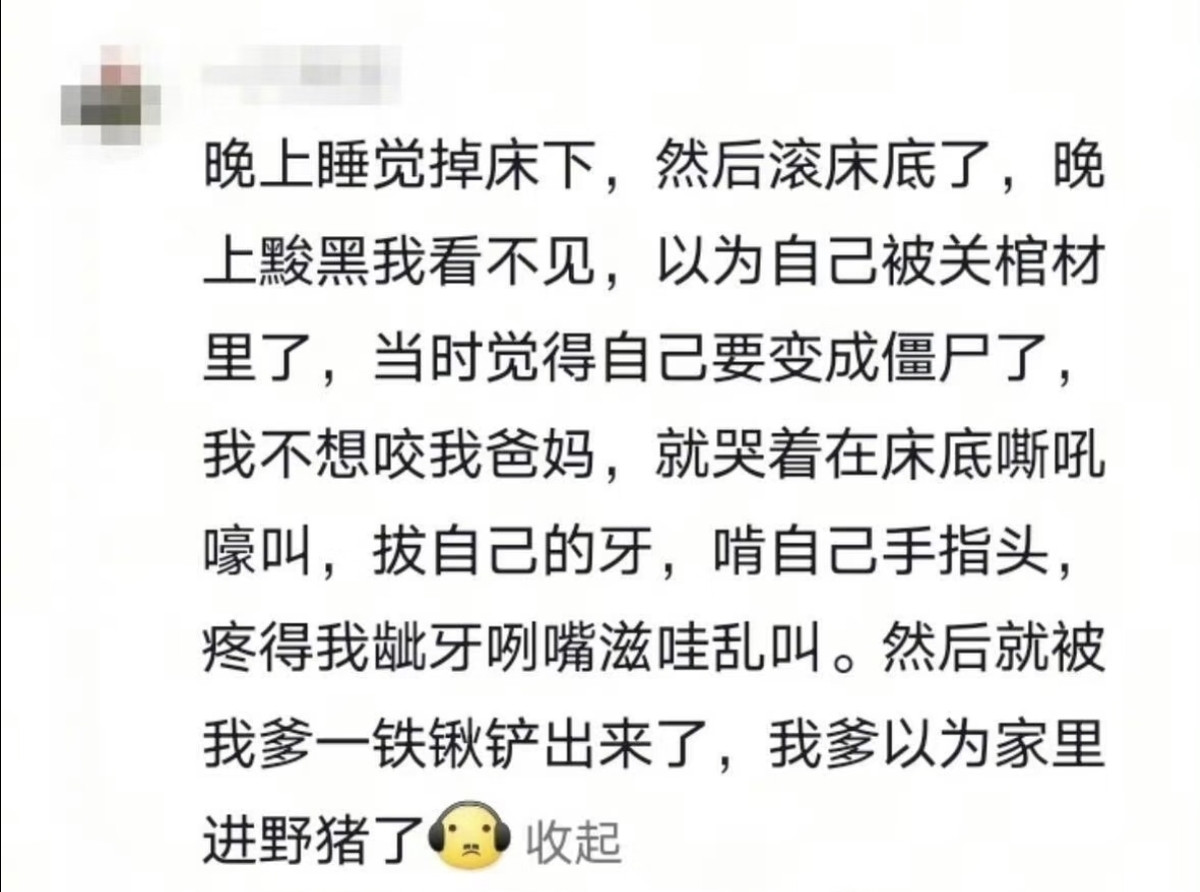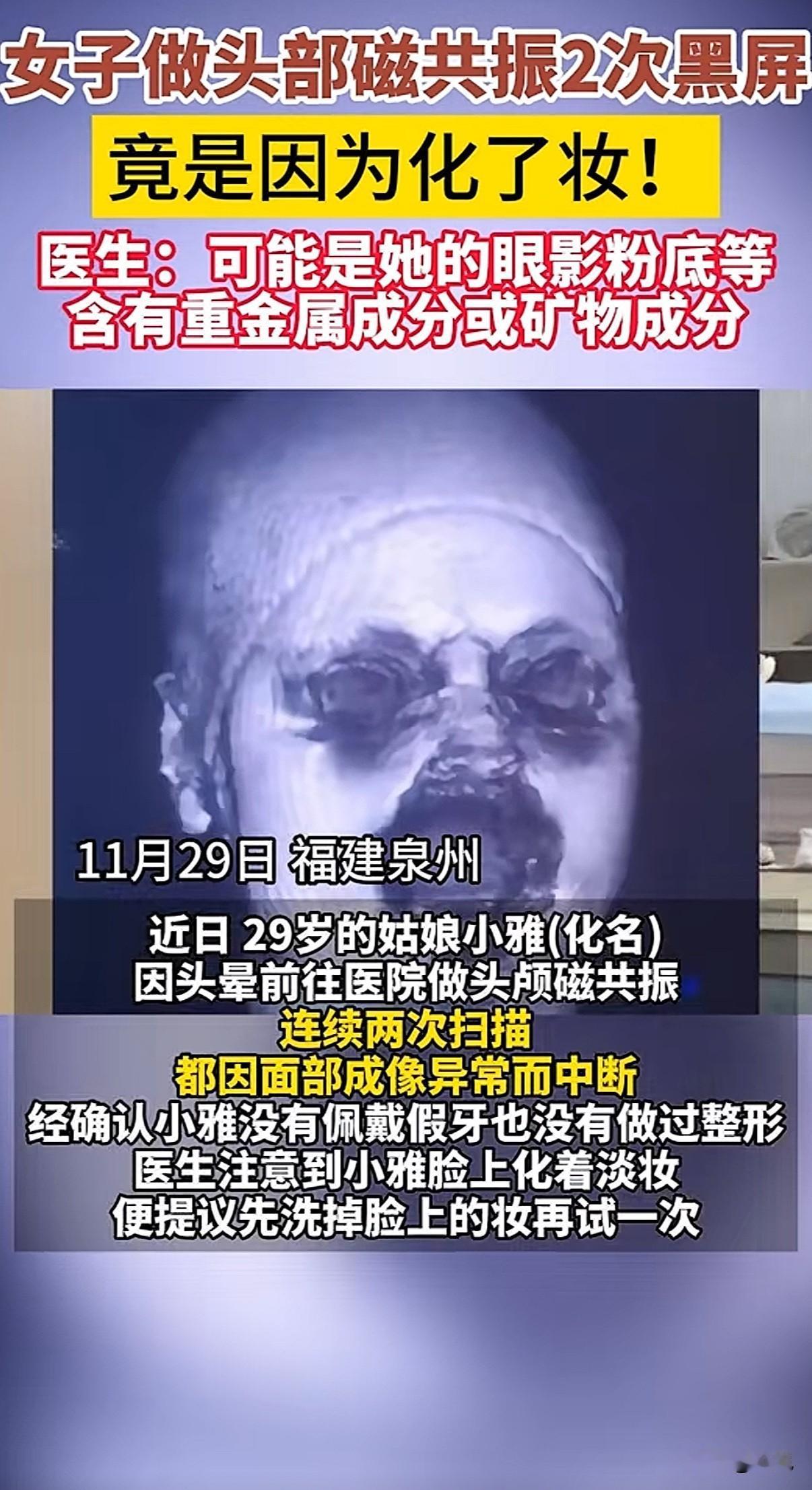昨天下午三点多,病房里特别安静,只有输液管里的药液滴答作响。我正帮爷爷削苹果,忽然听见隔壁床传来轻轻的动静——是那位总爱跟爷爷聊天的阿姨,她刚输完液,手还攥着针管贴在胸前,慢慢撑着床头想坐起来,腿刚一沾地又轻轻晃了晃。 昨天下午三点多,病房里静得能数清输液管里药液下坠的节奏,一滴,又一滴,敲在空荡荡的瓷盘里。 我坐在爷爷床边削苹果,果皮在刀刃上打着转,从红到黄,再到接近果核的浅白,像条没尽头的丝带,直到手腕酸了才发现——已经绕了小半圈盘子。 忽然隔壁床有响动,很轻,像羽毛擦过床单。 是那位总爱和爷爷聊家常的阿姨,她刚拔了针,左手还攥着棉签按在针眼上,右手撑着床头慢慢抬身,蓝白条纹的病号裤滑到脚踝,露出细瘦的小腿,刚想把脚放到地上,身子就轻轻晃了晃,像棵被风碰了一下的芦苇。 我手里的苹果刀顿了顿,果皮“啪”地断了。 她是不是等这一刻等了很久?刚才护士来拔针时说“您家属还没到?”,她笑着摆手“孩子加班呢,我自己能行”,可现在她咬着下唇,眼睛盯着床脚那双粉色的拖鞋,手指把床单捏出了几道褶子。 我放下刀走过去,扶她胳膊时才发现她手是凉的,针孔那里渗了点血,棉签早被汗浸湿了。“阿姨,我帮您。” 她愣了一下,赶紧抽回手想自己来,却被我轻轻按住:“没事,我爷爷这儿不着急,您先把鞋穿上。” 她的脚刚伸进拖鞋,就急着去摸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着,是张小男孩的照片,扎着羊角辫,举着颗红苹果。“想给囡囡拍张窗外的树,她上周视频还说‘奶奶,咱们楼下的玉兰该开了吧’,我这躺了三天,怕是赶不上第一朵了。” 我扶她站到窗边,阳光从玻璃斜切进来,刚好落在她银白的头发上,像撒了把碎金子。她举着手机对准窗外,手还在抖,我帮她托了下胳膊,镜头里的玉兰树果然有了花苞,鼓鼓囊囊的,像藏了春天的秘密。 “谢谢您啊孩子,”她按快门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光,“我家囡囡要是在,肯定也会帮你爷爷削苹果——她最会削这种长果皮了,说要给太爷爷绕个‘苹果项链’。” 我忽然想起前几天,爷爷总抱怨“隔壁太吵”,说阿姨从早到晚打电话,不是跟囡囡说作业,就是跟儿子说降压药怎么吃,可现在看着她手机里那个举苹果的小女孩,才明白那些絮絮叨叨里,全是没说出口的惦记。 回到爷爷床边时,苹果已经氧化出浅浅的褐边,我拿起来想重削,爷爷却摆摆手,咬了一大口:“甜的,比昨天的甜。” 他看着隔壁床,阿姨正对着手机打字,嘴角还翘着,阳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和爷爷的影子挨得很近,像两棵并排长的树。 输液管的滴答声好像变了调子,不再是单调的“嘀嗒”,倒像是谁在轻轻数着:一,二,三——春天快来了。
🌞2002年,60岁大妈出门遛弯,却发现路边有个孕妇正在捡垃圾吃。大妈出于
【4评论】【3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