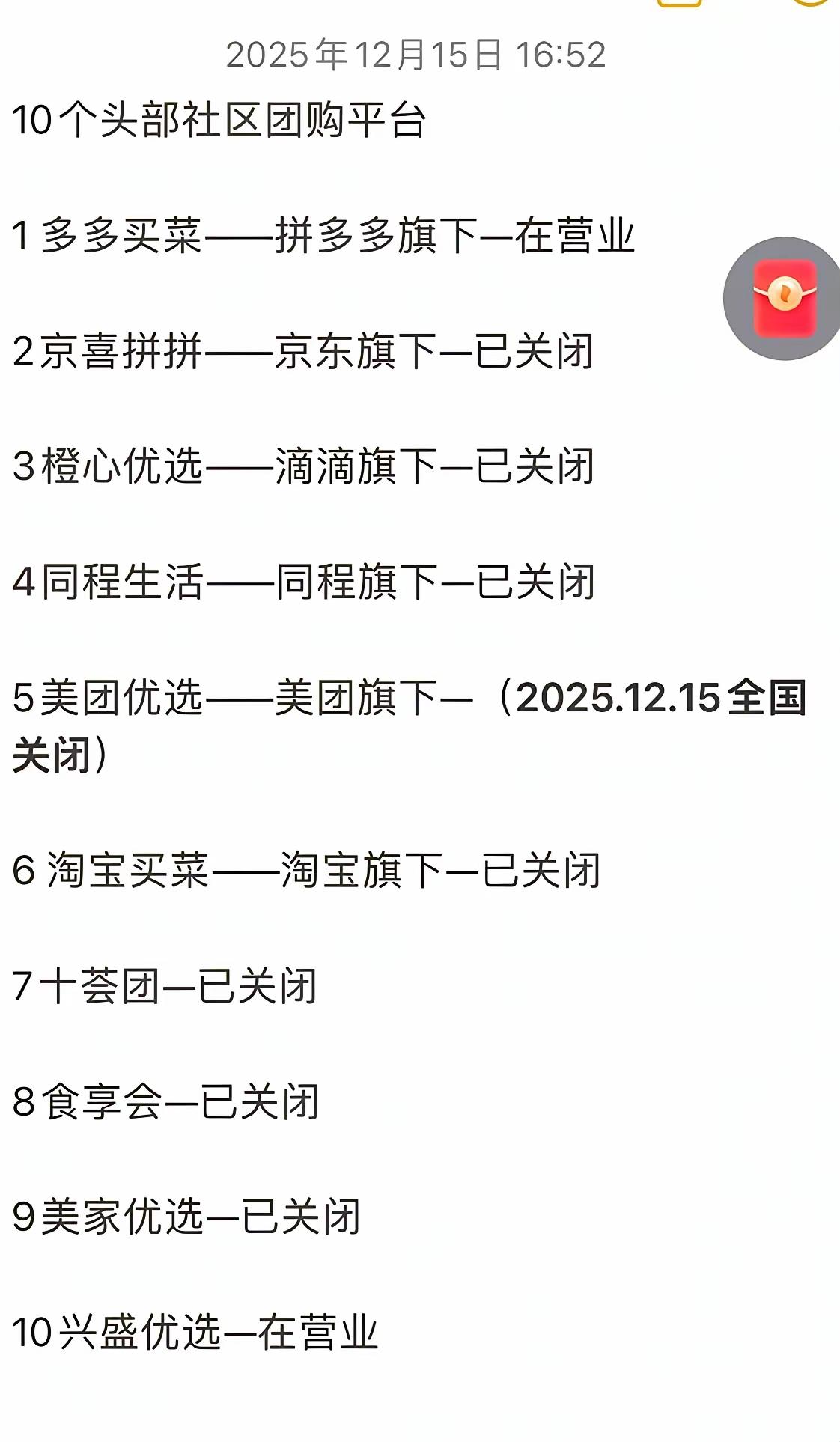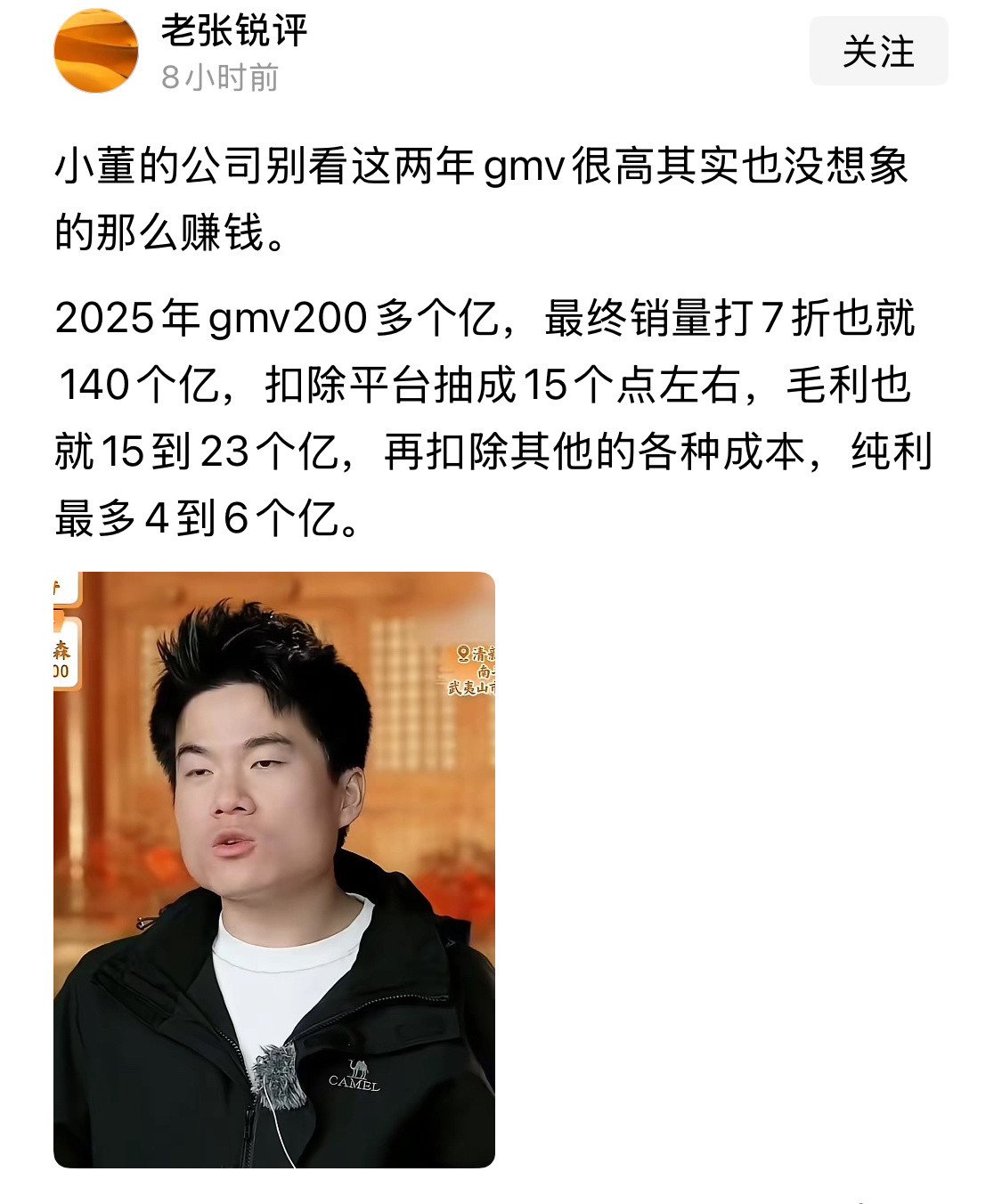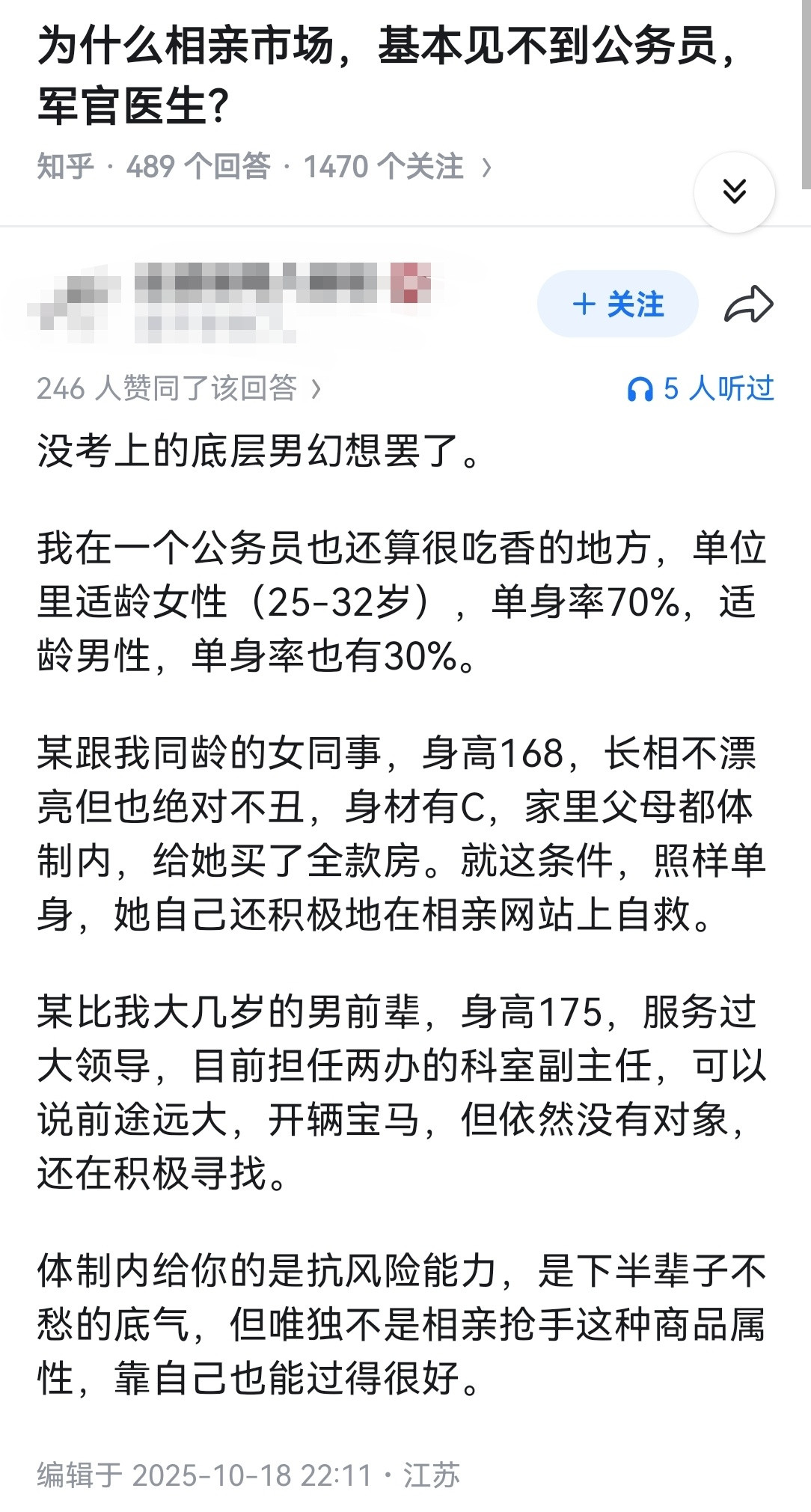17岁的我拿着妈妈借来的300块钱,6个煮的鸡蛋,3个苹果。踏上了绿皮火车,投奔姐姐们,南下深 攥着那300块钱的时候,手心全是汗。钞票被妈妈的手捂得温热,边缘都磨得起了毛边,她塞钱时反复念叨,说这是跟隔壁三婶和村头老李家凑的,让我到了深圳省着花,别跟姐姐们添麻烦。6个煮鸡蛋是凌晨四点就煮好的,蛋壳被我揣在怀里捂得温热,妈妈说路上饿了吃,顶饱还不用花钱。3个苹果是自家树上结的,挑了最大最红的,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怕挤坏了。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晃,车厢里挤得转不开身。汗味、泡面味、烟味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把装钱的手绢缝在内衣口袋里,手时不时摸一下,生怕丢了。对面坐着个大叔,看我一直低着头,递过来一瓶水,问我是不是第一次出门。我点点头,不敢多说,妈妈临走前嘱咐过,在外别跟陌生人搭话,人心隔肚皮。 火车开了两天一夜,我没舍得吃一个苹果,煮鸡蛋只啃了两个。剩下的要留给姐姐们,她们在深圳打工肯定不容易。夜里车厢里的灯暗下来,有人靠在椅背上打呼噜,有人小声说着话。我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心里又慌又期待。慌的是不知道深圳到底是什么样子,怕自己笨手笨脚,连份工作都找不到。期待的是听村里出去打工的人说,深圳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到钱,就能帮家里还债,就能让妈妈不用再为了几块钱跟人低头。 到深圳的时候是下午,太阳辣得晃眼。出站口挤满了人,举着牌子的,拉着行李箱的,吵吵嚷嚷。我攥着妈妈给的地址,东张西望,手心的汗把纸条都浸得发皱。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小名,一转头,就看见二姐冲我挥手,她比去年回家时黑了瘦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厂服,头发用皮筋随便扎着。 二姐接过我手里的蛇皮袋,埋怨我带这么多东西。我小声说,还有鸡蛋和苹果给你们。二姐眼圈红了,拉着我的手往公交站走。她说大姐在电子厂上班,要加班,晚上才能见着。她在制衣厂,管吃管住,就是活儿累,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 坐公交的时候,我扒着窗户看外面。高楼一栋挨着一栋,汽车跑得飞快,路边的树绿油油的,跟老家的黄土地完全不一样。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穿着土里土气的衣服,背着破旧的蛇皮袋,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到了二姐住的地方,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摆着两张上下铺的床,住了四个人。二姐说这已经算好的了,至少不用睡天桥。那天晚上,大姐下班回来,带了一份炒米粉,三个人分着吃。大姐说,厂里管饭,就是油水少,让我别嫌弃。我扒拉着米粉,眼泪掉在碗里,不敢让她们看见。 第二天,二姐带我去制衣厂面试。老板看我年纪小,又没经验,本来不想收。二姐好说歹说,说我手脚麻利,肯吃苦,老板才松口,让我先试试,工资一个月八百块,包吃住。 我就这样在制衣厂留了下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二姐学踩缝纫机。手指被针扎破了好几次,血珠子冒出来,我就用嘴吸一下,接着干。晚上下班,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躺在床上,浑身骨头都疼。可每次想到妈妈借来的300块钱,想到家里的债,想到姐姐们的不容易,我就咬着牙告诉自己,不能哭,不能怂。 日子一天天过,我慢慢熟练了,手脚也快了,工资也涨到了一千二。第一个月发工资,我寄了八百块回家,给妈妈写信,说我在深圳挺好的,吃得好住得好,让她别担心。其实我每天吃的都是食堂最便宜的素菜,住的是挤着四个人的小出租屋。 后来我在深圳待了很多年,换过好几份工作,从制衣厂到电子厂,再到后来自己摆摊卖小吃。我见过太多跟我一样的人,背着蛇皮袋,揣着借来的钱,从四面八方来,在这座城市里打拼。我们挤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啃着馒头就着咸菜,在流水线上重复着枯燥的工作,却从来没放弃过希望。 现在我在深圳买了房,把妈妈接了过来。偶尔跟她说起第一次来深圳的样子,她总会红着眼眶说,那时候苦了你了。我笑着说不苦,那300块钱,6个煮鸡蛋,3个苹果,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它们让我知道,人只要肯吃苦,肯坚持,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那些在绿皮火车上的颠簸,在出租屋里的拥挤,在流水线上的汗水,都不是白受的。它们刻在我的骨子里,让我明白,所有的光鲜亮丽背后,都是咬牙坚持的努力。这座城市从不辜负努力的人,就像生活从不辜负每一个勇敢奔赴的人。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