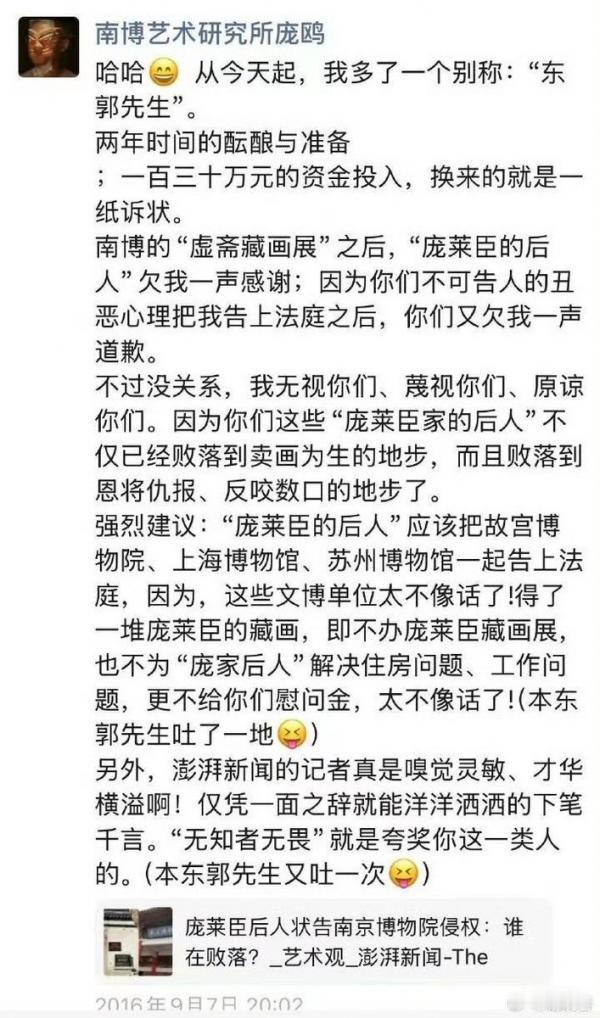1885年,胡雪岩病危,对九姨太说:“我死后葬礼上会来一个穿黑衣的人,到时剪下我寿衣一角给他,可保后事无忧,切记”。 油灯在杭州老宅的穿堂风里晃了晃,九姨太攥着男人枯瘦的手,没敢多问。 这位戴过红顶子的商人,此刻躺在窄小的木板床上,粗布被子盖不住嶙峋的骨头,哪还有半分当年“活财神”的模样。 三个月后,杭州城飘起冷雨,胡雪岩的葬礼比想象中更简单。 没有白幡如林,没有僧道诵经,一口薄棺停在门口,连油漆都没刷。 正当家人往灵前摆祭品时,巷口真的站着个穿黑衣戴铁帽的人,手插在袖筒里,盯着棺材一动不动。 九姨太想起那句嘱托,颤抖着剪下寿衣一角递过去。 黑衣人捏着那片粗麻布,突然叹了口气,转身消失在雨雾里。 后来才知道,那是城里有名的盗墓贼,见这光景,知道棺材里连块像样的玉佩都没有。 谁能想到,二十年前他还是紫禁城骑马的红顶商人。 左宗棠要西征,国库空得响,是他一趟趟跑上海,跟洋行借了六笔银子,硬生生凑齐了军饷。 朝廷赏了布政使衔,黄马褂穿在身上,连王爷见了都得喊声“胡大人”。 那时候他的阜康钱庄开遍大江南北,库房里的银子多得能堆成山,谁会料到最后要靠一件布衣挡盗墓贼。 转折是从光绪八年开始的。 他看着洋商把生丝低价收走,心里堵得慌,一口气囤了一万四千包生丝,想把价格抬起来。 可那些洋行老板抱团不买,李鸿章那边又总有人放风说他钱庄要倒闭。 挤兑的人从钱庄门口排到街尾,他拆东墙补西墙,最后连胡庆余堂的药材都抵押了出去。 红顶子被摘那天,他坐在空荡荡的账房里,把算盘摔成了两截。 出殡前,九姨太问要不要请戏班,他摇头;问要不要修祠堂,他还是摇头。 “就穿这件旧棉袍,棺材薄点没事。” 他说这话时,眼睛望着窗外的胡庆余堂,那是他这辈子最上心的买卖,“真不二价”的牌匾擦得锃亮。 后来《杭州府志》里记,这场葬礼只花了八十两银子,比当时一个小掌柜的葬礼还简单。 对比盛宣怀母亲葬礼花的十万两,他像是故意要跟那个浮华的世界划清界限。 现在杭州胡庆余堂的后墙,还嵌着块“戒欺”的石碑,是他当年亲笔写的。 游客路过时大多匆匆一瞥,没人知道这四个字背后,藏着一个商人从红顶辉煌跌落后的清醒。 就像那件被剪下一角的寿衣,粗布底下,是他用一辈子看懂的道理:权力和银子都是过眼云烟,唯有守住本心,才算没白来这世上走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