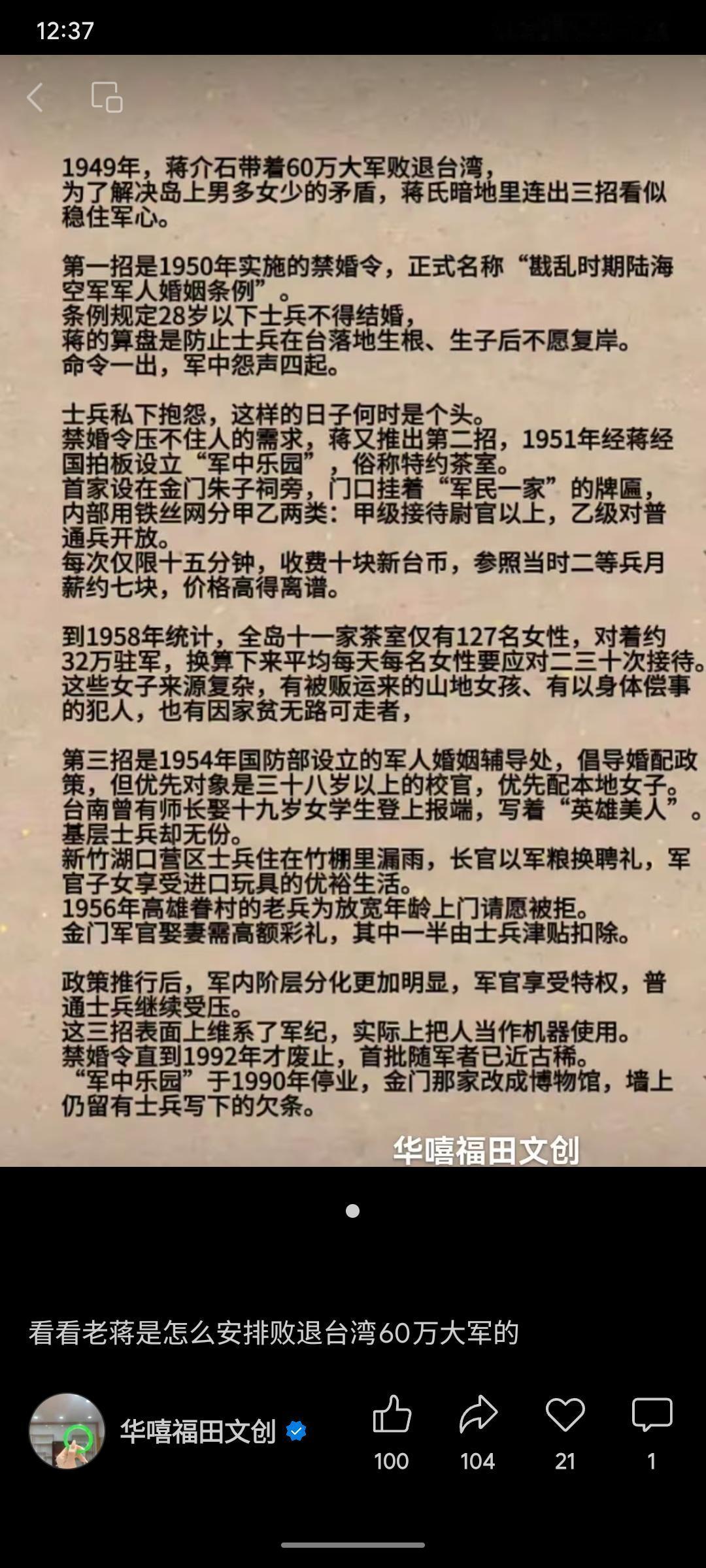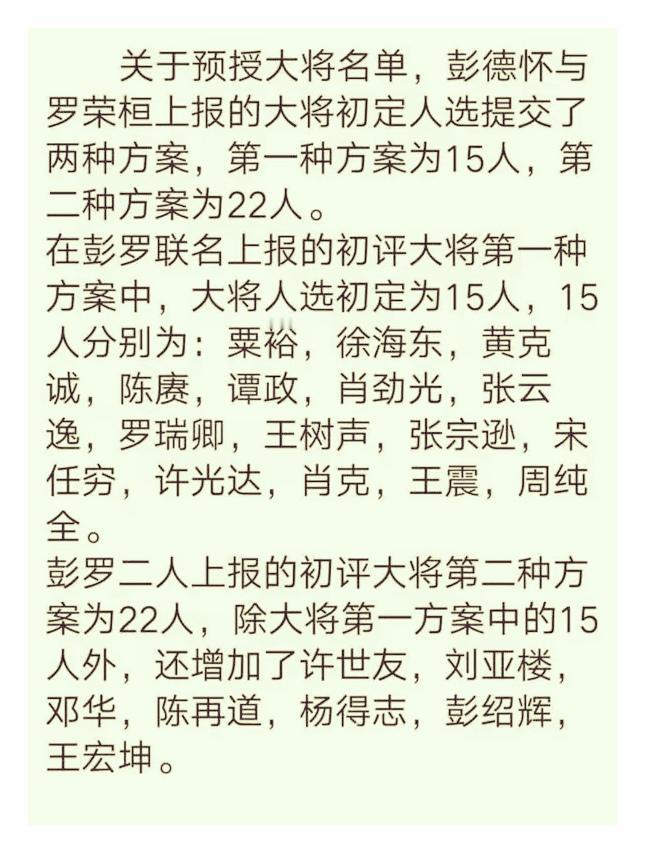1929年,一叛徒来找柯麟看病,柯麟当即认出了叛徒,但他没露声色,不慌不忙地给叛徒看完病,然后以取药为名,暗地里派人通知中央特科。 搭在腕关处的那三根手指,本该是救死扶伤的探针,那一刻却成了复仇者的准星。 1929年的上海深秋,寒意已经能透进骨缝里,法租界的达生医院诊室内,空气静得如同凝固的胶水。坐在问诊台前的柯麟,脸上挂着那一贯温厚儒雅的职业微笑,只有他自己知道,胸腔里的心脏正在那一秒猛然撞击了一下肋骨。 坐在对面的“病人”并不是陌生人,哪怕此人脸色惨白、高烧得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柯麟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双闪烁着极度惊恐与猜忌的眼睛。 他是白鑫——那个刚刚背叛组织、将彭湃等四位昔日战友推向刑场的罪魁祸首。作为彭湃的老同学和引路人,柯麟此刻距离这个血债累累的叛徒,中间只隔着一张不到一米宽的诊桌。 仇恨几乎要在瞬间冲破血管,但多年地下工作的淬炼,像一剂强力的镇静剂,将柯麟的情绪在那千分之一秒内强行冻结。诊脉的手指稳如磐石,没有任何多余的颤动,仿佛手指下跳动的不是一个必须铲除的毒瘤,而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疟疾患者。 这场特殊的“手术”,在脉搏的跳动中拉开了帷幕。 对于白鑫来说,身体的剧烈痛楚和内心对红队(中央特科行动科)锄奸的极度恐惧,让他处于崩溃的边缘。他像一只受惊的困兽,即便看病也不敢完全卸下防备,眼神在诊室的四角和窗外疯狂游移。 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位有着精湛医术、在弄堂百姓口中有口皆碑的“仁医”,早在1924年就已经把手术刀和信仰熔铸在了一起。 为了稳住这个惊弓之鸟,柯麟不但没有加快速度,反而故意放慢了节奏。他一边温和地询问病情,将其归结为急性病症,一边起身走向药柜。在转身背对白鑫的瞬间,医生的角色褪去,情报员的本能接管了身体。 借助取药、称量和包装这几个常规动作的视线遮挡,柯麟从白大褂口袋里飞速掏出一张预藏的微型纸片,用藏好的铅笔匆匆写下预警密语,指尖灵活地将纸片反复对折,神不知鬼鬼不觉地塞进了药盒的最底层。 在给药盒贴标签时,他又用指甲盖在边缘隐晦地划了一道极浅的印痕——那是给交通员的死亡坐标。 “按时服药,注意静养。”转过身时,柯麟递过去的不只是一盒用来退烧止痛的药剂,更是一道无形的催命符。 白鑫抓过药盒付了钱,甚至等不及细问,便像躲避瘟神一样匆匆消失在街角的阴影里,这种过度的警惕反倒成了最大的破绽,证明了他的藏身之地就在附近,且病得只能就近求医。 而柯麟也没有片刻停歇,那盒带着刻痕的药,很快就通过前来的交通员,流转到了中央特科陈赓的手中。药盒底部的纸条展开,猎人锁定了猎物的方位。 但真正的博弈,此时才刚刚进入深水区。 由于病情并未因这一盒药彻底根除,加上在这座城市里他根本不敢信任其他陌生面诊,走投无路的白鑫不得不多次请求柯麟出诊,这时候的医生身份,成了柯麟手中最锐利的“通行证”。 他提着出诊箱,顺理成章地踏进了白鑫那个戒备森严的最后堡垒——位于霞飞路和合坊的范争波公馆。 如果在诊室里拼的是演技,那么在这里拼的就是洞察力。每一次看似平常的上门复诊,其实都是一次精密的军事侦察。柯麟一边给白鑫把脉、开方,调整着药物剂量来控制对方的身体状态,一边不动声色地用余光扫描着整座公馆的安防布置。 门岗的换班频率、警卫的站位死角、楼层撤离的通道走向,全被他那双看似关注病情的眼睛,像照相机底片一样一一印刻在脑海里。 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接触,甚至麻痹了白鑫最后的一丝防线。在这个他认为唯一能缓解病痛的“老熟人”面前,白鑫的心理防线随着身体的好转反而出现了松懈,他在闲聊中无意间透露了自己即将在11月11日离沪、逃往意大利避难的核心机密。 那一刻,柯麟知道,收网的时间到了。这张用医术编织的天罗地网,终于勒紧了最后一个绳结。他没有流露出一丝兴奋,依然平静地开完了最后的处方,实际上是将这一绝密情报第一时间传递给了负责执行的红队。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凛冽的风没有吹散和合坊附近的杀气,当白鑫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走出寓所,准备踏上逃亡之路时,早已埋伏在暗处的红队队员如同天降神兵。 枪声划破了法租界的宁静,也彻底击碎了叛徒苟活的幻想,白鑫及其党羽当场毙命,第二天上海《民国日报》头版那条震惊全城的暗杀新闻,给这段隐秘的较量画上了一个暴烈的句号。 在那件悬壶济世的白大褂之下,柯麟把悲痛嚼碎了咽进肚子里,用极致的冷静做引线,引爆了针对背叛者的雷霆一击。在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听诊器既能听到病患的心跳,也能听清时代的暗流。 信源:搜狐资讯——《风与潮》柯麟瞒天过海!原来,这才是柯正平安全送出抗战物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