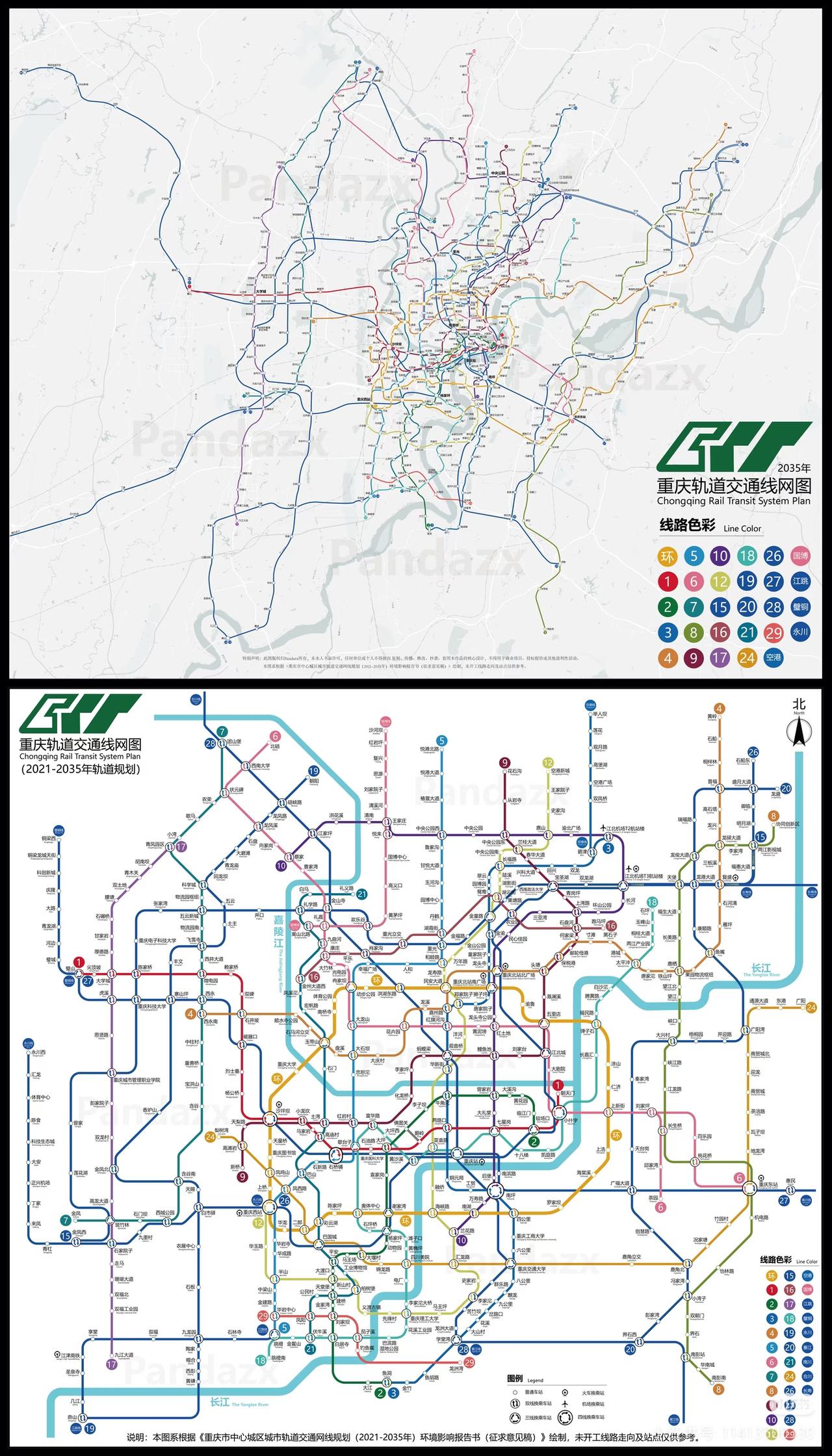1937年的一个凌晨,重庆的巡逻士兵忽然发现城外来了一群赶牛的人,这群士兵心里不禁嘀咕道:这是什么人,怎么这么早就出来放牛了?他们不知道,这些穿着沾满泥点衣服的“放牛娃”,其实是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师生,赶着的也不是普通牲畜,28头荷兰乳牛、15头约克夏种猪,还有200多只家禽,每一口喘气都连着中国农业科学的未来。 那年冬天南京已经能听见炮火声,中央大学决定西迁重庆。 农学院的动物是从美国引进的珍贵品种,王酉亭带着12个饲养员说“中国的种,不能留给日本人”。 原计划走长江水路,3艘木船都联系好了,可没等出发,芜湖陷了,日军把长江航线掐断了。 他们只能改走陆路,1200公里,靠脚底板和木笼子,把这些“活教材”送后方去。 出发时带了500公斤混合饲料,200米帆布搭防雨棚,兽医李培元还备了10个急救箱。 王酉亭给队伍分了组,饲养组管喂食,医疗组看牲口健康,警戒组负责探路。 每天最多走25公里,到点就得歇,牛要吃草,猪要喂糠,比照顾人还仔细。 有员工抱怨过“人都快饿死了,还管这些畜生”,王酉亭没骂他,只是把自己的窝头掰了一半给那头怀崽的荷兰牛。 过江汉平原时最难。 1938年正月里,云梦泽的沼泽地冻得硬邦邦,太阳一出来又化成烂泥。 3头种猪陷在泥里直哼哼,几个人跳下去用肩膀扛,泥没到大腿根,硬是把猪抬到干地上。 晚上宿营,李培元用青蒿和板蓝根熬了大锅汤,给牲口灌下去,“人病了能扛,它们病了,一路就白走了”。 后来这方子还登在了当时的《畜牧兽医月刊》上。 最险的是在宜昌外围。 1938年3月17日上午,9架日军飞机突然俯冲下来。 炸弹在畜群旁边炸开,饲养员陈阿毛扑在一头牛身上,气浪把他掀出去老远。 等硝烟散了,4个兄弟没起来,12只鸡被炸死了。 王酉亭抱着流血的种猪“爱国号”,手都在抖,可还是咬着牙说“走,接着走”。 那天晚上,他们摸着黑把牲口转移到山坳里,谁都没合眼。 16个月后,这支奇特的队伍终于走到了重庆沙坪坝。 荷兰乳牛从28头繁育到87头,成了大后方医院和学校的奶源;约克夏种猪和本地猪杂交出的“川东黑猪”,让肉产量提了不少。 直到抗战胜利,这些动物没少一头核心品种。 现在南京农业大学还留着“爱国号”的标本,标签上写着“1938-1946,见证一场用脚步丈量的坚守”。 那天清晨重庆城外的牛群,后来在沙坪坝农场的栏里生下了一代代小牛。 王酉亭晚年回忆时总说,最难忘的是过沼泽地时,大家喊着号子抬猪的声音。 其实哪有什么奇迹,不过是一群人把“不能让学术断了根”的念头,一步一步走成了1200公里的路。 那些被精心照料的牲畜,早把这段历史嚼进了骨头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不会褪色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