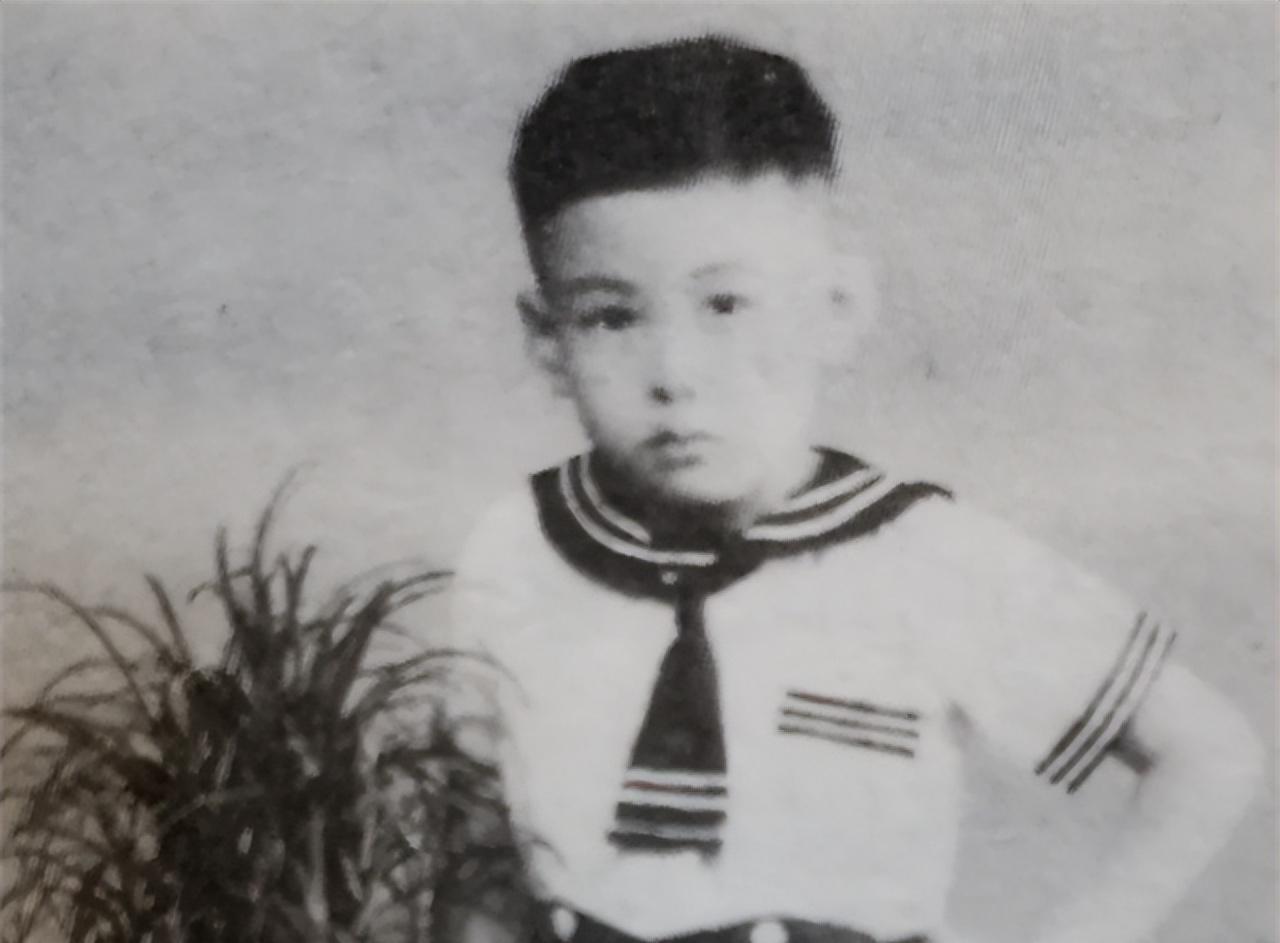1983年5月23日中午,张灵甫的外孙鲁航放学回家,一进门便吓傻了。 屋里静得反常,母亲常坐的藤椅空着,桌上的搪瓷杯还冒着余温,那条她最喜欢的红色围巾随意搭在沙发扶手上,像团凝固的血。 鲁航喊了两声没人应,书包滑落在地。 邻居李阿姨匆匆跑来,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诊断书。 "你妈上午被送医院了,"她声音发颤,"医生说...吃了太多降压灵。 "外婆王玉龄赶到医院时,抢救室的灯已经亮了两个小时,护士进出都低着头。 后来才知道,母亲张惠君那段时间总失眠。 1979年她申请平反时,档案袋上那句"其父属国民党战犯,不予纠正"像根刺,扎了四年。 上个月厂里通报她挪用公款58元时,她把自己关在房里一整天,出来时眼窝陷得吓人。 我觉得,那瓶降压灵或许早成了她对抗生活的武器,只是那天用错了方式。 外婆王玉龄总说,1947年孟良崮战役后,她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在南京码头等船,手里攥着张灵甫留下的佩剑照片。 1952年生张惠君时,她特意给女儿取小名叫"念慈",却在那个年代成了不敢示人的秘密。 有次整理旧物,我发现母亲入团申请书上"家庭成分"栏被划得漆黑,纸背都磨破了。 南京三中的档案里还留着1969年的记录,母亲因为"历史问题"没入团。 其实那时她每天最早到教室擦黑板,冬天手冻得裂开口子也不停。 去年在上海见到黄百韬的女儿黄慧南,她说那时候她们这些"战犯后代",连跳皮筋都要躲着红卫兵。 现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还锁着那个用降压灵药瓶改的钢笔。 1988年心理治疗时,医生让我把最害怕的东西变成纪念品。 上周去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说要展出它。 玻璃柜里的药瓶标签已经泛黄,但阳光照进来时,瓶身折射的光斑像极了母亲年轻时的笑容。 那天闭馆前,我又看了眼展柜里的药瓶钢笔。 标签上"降压灵"三个字被磨得快看不见,瓶口缠着的蓝布条却还是鲜艳。 外婆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在雾里走,有时候看得见前面的灯,有时候看不见。 现在想来,母亲当年大概是把那灯光当成了别的东西,走错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