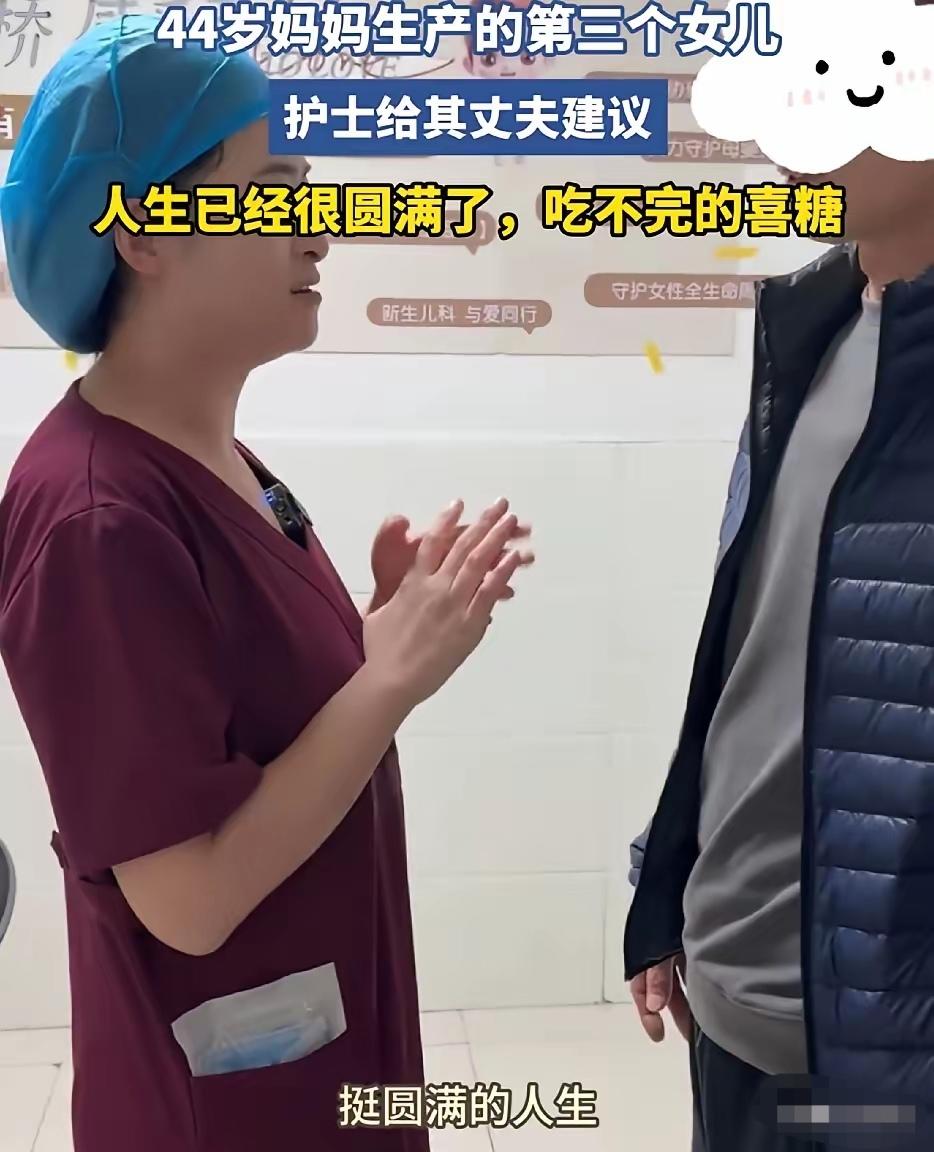1969年,一名女知青去到北大荒,10年过后,当众人返回家乡时,她却放弃了返程机会,决定留下来做农民。 那列载着返城知青的绿皮火车鸣笛时,黄丽萍正蹲在麦田里捡麦穗。 同批来的姐妹扒着车窗哭,她却把刚发的返城证明塞进灶膛,火苗舔着纸片,像在烧她12年的青春。 没人懂,这个陕北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放着城里的铁饭碗不要,偏要守着这片黄沙地。 刚到北大荒那年,冬天冷得能冻裂水缸。 黄丽萍裹着打补丁的棉袄学割麦,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又结茧,有老乡劝她“城里姑娘遭这罪干啥”,她却连夜帮人家写了封家书,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后来她用大学辅修的医术给冻伤的娃治冻疮,药箱里总装着自己熬的冻疮膏,味道苦得很,却比供销社的药膏管用。 春耕的拖拉机陷进泥里时,是刘成轩跳下去扛着轮子推。 这个贫农子弟的手比老树皮还糙,却能把报废的农机零件拼出能用的犁。 黄丽萍教他认拖拉机说明书上的字,他教她分辨哪片土适合种大豆,后来两人蹲在田埂上啃窝头,他说“这地要是有文化人带着干,准能多打粮”,她没说话,却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第一页。 父亲坐了五天五夜火车来劝她,看到她住的土坯房时红了眼。 “你爷爷当年就是因为成分问题被批斗的,现在回城才有活路!”他把国企招工表拍在桌上,黄丽萍却翻开那本写满农业笔记的本子,指着里面画的水库草图:“爹,你看这水浇地,去年收的粮食够全村吃半年,我走了,谁教他们用新机器?”那天夜里,父亲摸着她手上的老茧,叹了口气没再提回城的事。 1981年春天,政策松动的消息像风一样刮过农场。 同批知青收拾行李时,黄丽萍却在院子里搭起了夜校的木牌。 她把自己的返城名额让给了家里困难的知青,转身带着村民分组包地种麦子。 那年冬天,她家烟囱总冒到后半夜,煤油灯底下,她教妇女们认字,教后生们算产量,黑板上写的“科学种田”四个字,被炉火映得暖烘烘的。 如今黄丽萍的孙子在农大读研究生,每次回来都要翻奶奶那本泛黄的《农业技术手册》。 手册里夹着1982年的麦种标本,还有她和刘成轩当年画的农具改进图。 前阵子村里通了互联网,老人学着用手机看孙子发的农场视频,笑着说:“你爷爷当年修拖拉机,你现在鼓捣无人机,这地啊,认的不是啥新鲜玩意儿,是肯下力气琢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