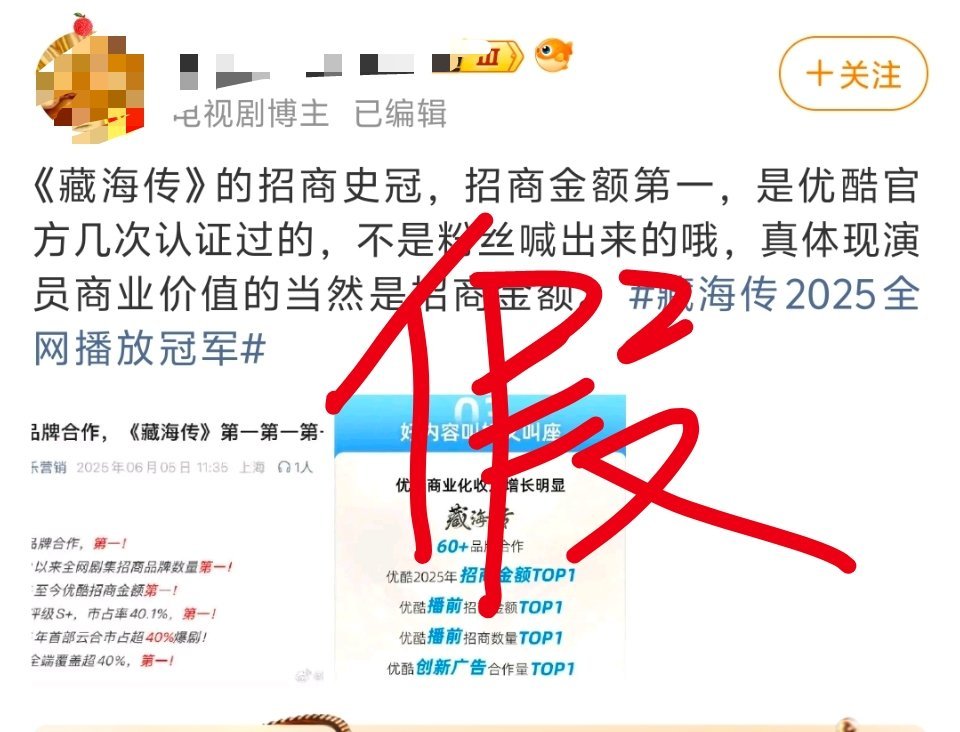王老师的教鞭是根枣木棍子,被手汗浸得油亮,挂在黑板旁边的钉子上,像条随时会窜起来的蛇。我们班四十多个孩子,没人没尝过那棍子的滋味——背不出乘法表的,手心得肿三天;作业本上有错别字的,罚站时还得被抽后背;最惨的是上课走神的,她会突然从讲台后面绕过来,一棍子敲在桌腿上,震得铅笔盒“哐当”响,魂儿都能吓飞。 王老师的教鞭是根枣木棍子,被手汗浸得发亮,挂在黑板边的钉子上,阳光斜斜照过来,油光里能看见密密麻麻的细纹路,像条蜷着的老蛇。 我们班四十多个小萝卜头,没人没跟那棍子打过照面——手心、后背、桌腿,它落在哪儿,哪儿就带着枣木的腥气。 背不出乘法表的,她捏着你手指根,教鞭“啪”地抽在掌心,疼得你直抽气,眼泪掉在课本上,晕开一小团湿痕;作业本上有错别字的,罚站时脊梁骨得绷直,她从背后过来,棍子扫过衣服,“嗖”的一声,麻劲儿能窜到后脑勺;最吓人是上课走神,她不说话,悄没声从讲台后面绕过来,一棍子敲在桌腿上,铅笔盒“哐当”翻倒,橡皮滚到过道里,魂儿都能吓飞半条。 三年级那年冬天,我把“乘以”写成“乘于”,作业本发下来时,王老师的红钢笔在那字上画了个圈,旁边写着“放学留一下”。 那天我攥着作业本站在讲台边,她没说话,先把教鞭从钉子上取下来,枣木棍子在手里转了两圈,“啪”地敲了下讲台,粉笔灰簌簌往下掉,我盯着自己磨得起毛的袖口,数着地砖缝里的灰。 “知道错哪儿了?”她突然问,声音不高,却像教鞭敲在心上。 我小声说“乘于”写错了,她嗯了一声,教鞭抬起来,我下意识缩脖子,却没等来疼——棍子轻轻碰了碰我的作业本,“这字笔画简单,可考试时错一个,就是一分,一分能差多少名次?现在疼点,总比以后哭着说‘要是当初’强。” 后来我才知道,隔壁班的李老师总说王老师“狠心”,可我们班的数学平均分,连续三年都是年级第一;那些被她敲过桌腿的走神鬼,后来上课都坐得笔直,眼睛瞪得像铜铃——是怕吗?或许有,但更多的是知道,那棍子落下的地方,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 因为怕那棍子敲手心,我把乘法表抄在铅笔盒里,早晚背,直到现在闭着眼都能背到“九九八十一”;因为怕她抽后背时的疼,我每次写作业都用尺子比着,错别字?整个小学阶段,我的作业本上红叉都少得可怜。 你说那教鞭是凶器吗?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是,可现在想起王老师转着枣木棍子的样子,怎么倒有点像握着根定盘星? 那时候手心肿着不敢握笔,夜里偷偷哭,觉得她是全天下最凶的老师。 后来上了中学,再没人用教鞭盯着我写作业,可那些被打出来的习惯——认真、专注、不马虎,倒跟着我走了很多年。 或许教育从不是只有温柔一种样子,就像那根枣木教鞭,看着吓人,却在我们这群野小子心里,刻下了最实在的规矩。 现在路过小学教室,黑板旁边的钉子早没了,可我总觉得,那里还挂着条发亮的枣木棍子,不是蛇,是枚老印章,在童年的纸上,盖了个沉甸甸的戳:不许糊弄。
王老师的教鞭是根枣木棍子,被手汗浸得油亮,挂在黑板旁边的钉子上,像条随时会窜起来
小杰水滴
2025-12-30 17:28:30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