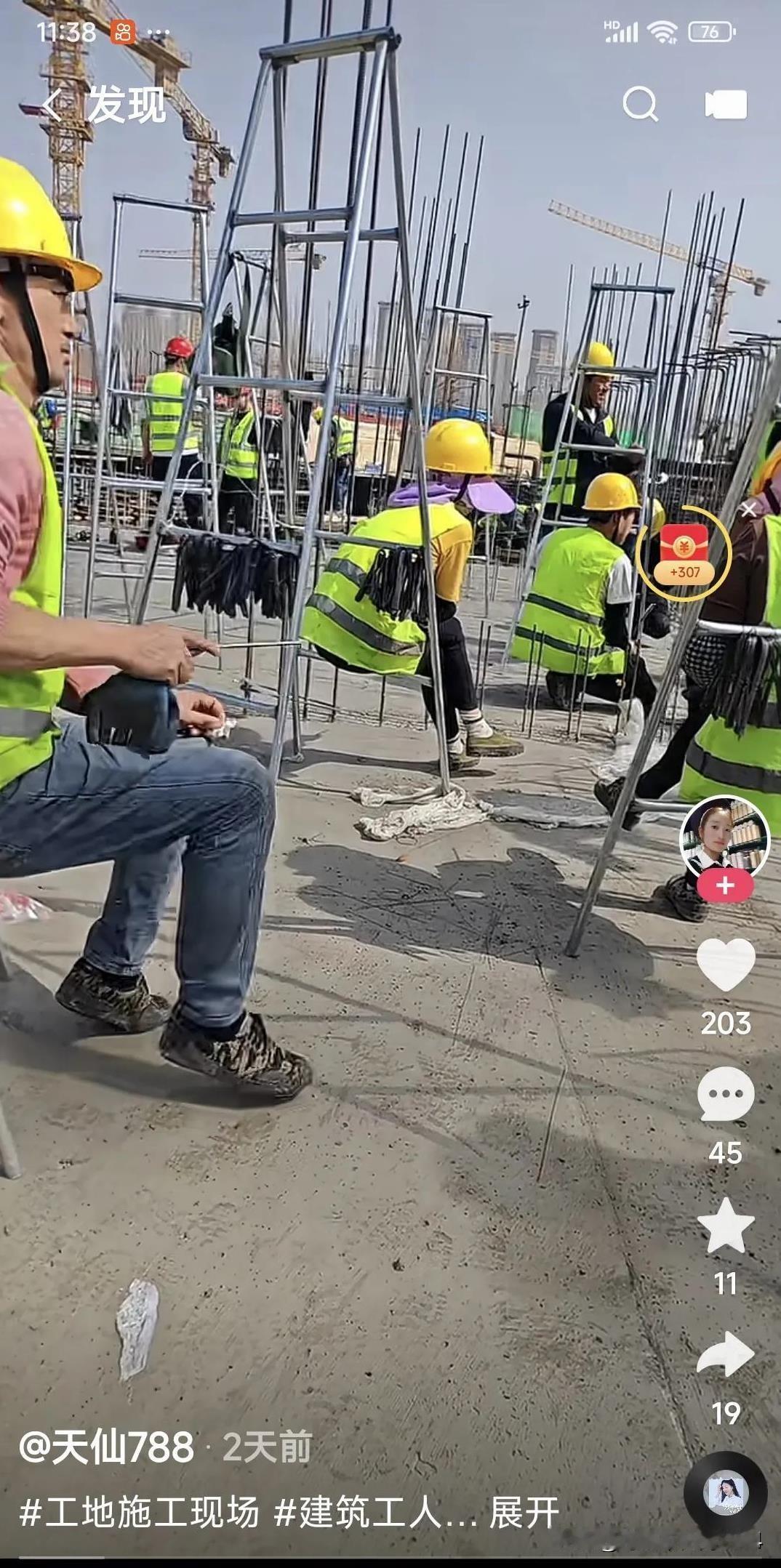有一年,有个生产队一个同姓的小姑娘未婚先孕,因为不显怀,七八个月才被发现。打骂也不说是谁,小姑娘的父母就找到外公,满脸愁容问他:叔,这事咋办;打掉吧,都快生了,搞不好一尸两命。生下来,就是养一辈子,也被人戳脊梁骨。 外公让姑娘住进了自己村东头的土屋。那阵子,他晌午收工回来,总从怀里摸出个温热的煮鸡蛋,搁在灶台上。姑娘就默默剥了吃。屋里静,只有老挂钟滴答响。 孩子生下来那天,是个雨夜。外公蹲在堂屋抽旱烟,烟头的红点在黑暗里一亮一暗。后来接生婆喊他进去,他看见姑娘虚汗湿透了头发,身边躺着个皱巴巴的小肉团。他什么也没问,转身去灶上搅了一碗面糊糊。 满月前后,村里闲话最多。有天傍晚,一个外乡货郎路过,在井边歇脚,跟人闲聊时瞥见了在院里晒尿布的姑娘。货郎三十来岁,瘦高个,说话带着山那边的口音。之后几天,他总“恰好”经过村东头,有时递块麦芽糖,有时放下两把新摘的野莓。 外公看在眼里,没作声。直到那天货郎拎着半斤红糖上门,支支吾吾说,他走南闯北,缺个屋里人,不介意带孩子。外公正编竹筐,头也没抬:“她不是件货。” 货郎讪讪走了。那天夜里,外公对姑娘说:“路得自己挑,但别因为难,就跳进看着容易的坑。”姑娘望着油灯,眼泪啪嗒掉在孩子襁褓上。 孩子快百日时,货郎又来了,这回直接说可以带她们娘俩走,去山那边,没人认识。姑娘抱着孩子,在门槛边站了很久。夏天的风吹得杨树叶哗哗响,知了叫得人心慌。最后她摇了摇头,声音很轻:“这儿再难,也是根。” 货郎再没出现。姑娘开始跟着外公下地,孩子用布带绑在她背上。她学得快,割麦子不比别人慢。村里人起初指指点点,后来见她埋头干活,汗珠子砸进土里,闲话也渐渐少了。 孩子会走路那年,姑娘用攒的布票换了块蓝底白花的布,给自己做了件新褂子。穿着它去镇上卖鸡蛋,有人问起孩子爹,她笑笑说,在远方干活呢。阳光照在她脸上,平静得很。 外公老了,腰弯得更深。姑娘每天收工先到他屋里,劈柴挑水。孩子跟在后面,咿咿呀呀叫“太公”。有天傍晚,外公坐在门槛上,看姑娘在院里喂鸡,孩子追着鸡崽跑。他摸出旱烟,却没点,就那么握着。 很多年后,那孩子长大了,去外地读书。有年暑假回来,陪老人乘凉,忽然问:“太公,您当年为啥肯帮我们?”外公摇着蒲扇,眯眼看了会儿天上的星星,说:“人啊,就像地里的苗,有的长得慢些,有的被风吹歪了。可只要根还在土里,总能站起来。” 孩子似懂非懂。这时姑娘——如今已是头发花白的妇人——端着切好的西瓜从屋里出来,轻声接了一句:“你太公是怕我们娘俩,当时根要断了。”夜风吹过院子,带来远处稻田的气息,一阵凉,一阵香。
泪目!一对年轻夫妻,怀孕时在检查室看到宝宝脸上有一道黑影,医生说可能是胎记,丈夫
【9评论】【5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