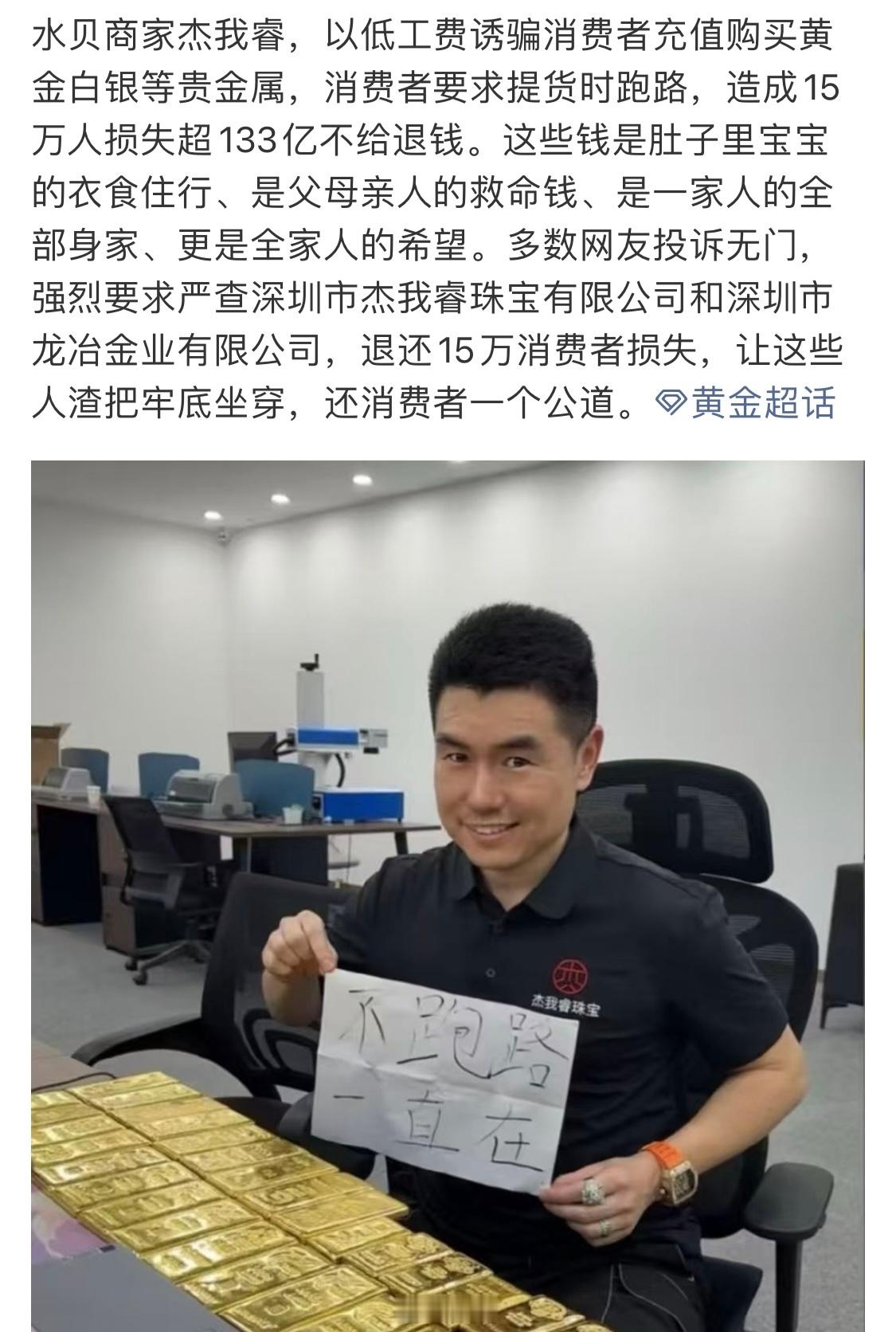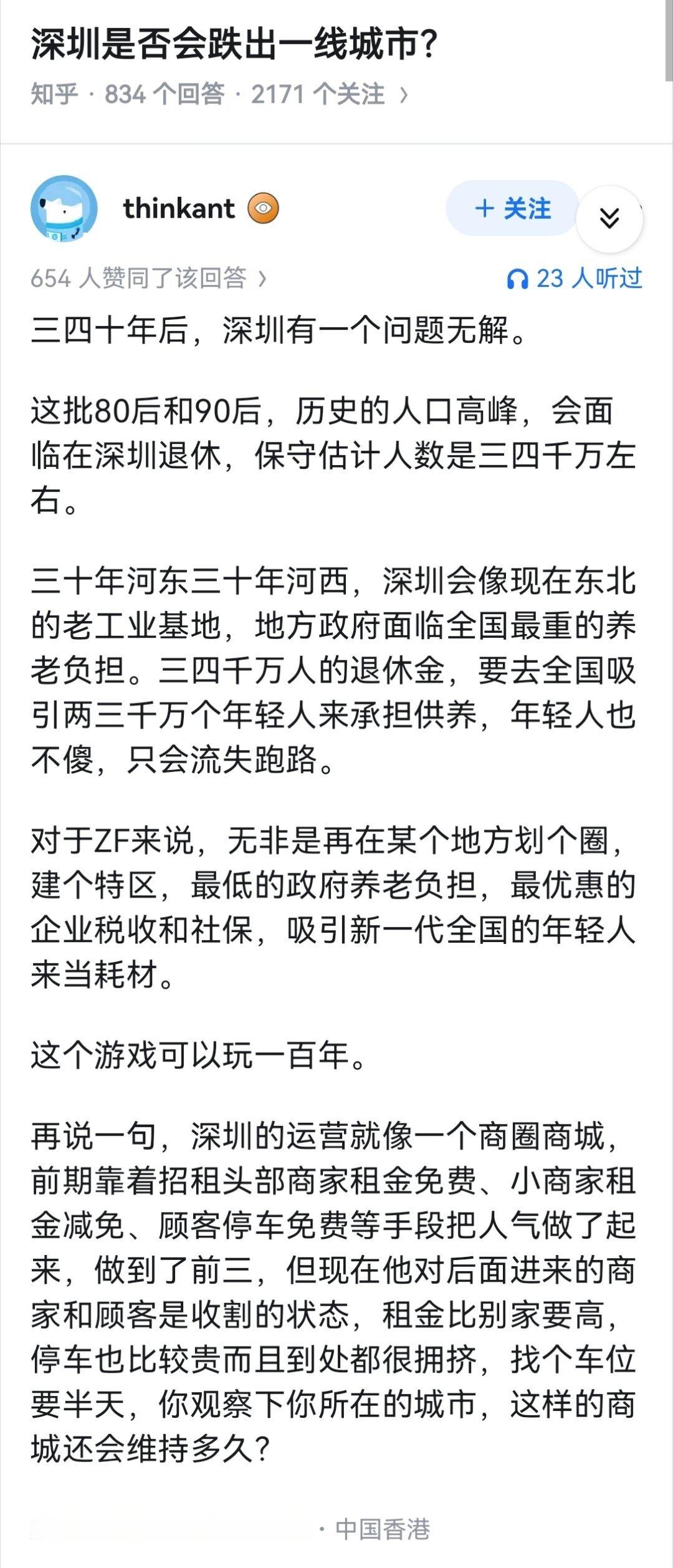我大姑年轻时骗了我奶奶的棺材本去深圳做生意,发了财在那边安了家,我奶奶瘫在床上三年她没回来看过一次,连电话费都不舍得给老人充。去年深秋,村口的老槐树落了满地叶子,大姑的黑色轿车就停在树底下,车身上还沾着深圳的泥点子。她穿着一身皮夹克,身后跟着个拎公文包的律师,一进村委会就拍桌子:“我妈当年亲口说过,老宅东边那半亩地给我,你们得认!” 村支书叼着旱烟袋没抬头,手里的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地的事好说,但你先跟我去个地方。”大姑脸涨得通红,刚要掏怀里的房产证,被村支书摆手拦住:“别拿那些城里的玩意儿说事,先跟我走。” 她拧着眉跟在后面,律师想跟上,被村支书眼一瞪:“这儿是农村,轮不到你插嘴。”没多远就到了村西头的坟地,奶奶的坟头草刚被我爹铲过,新土还露着黄。村支书指着坟头:“你娘咽气前三天,还攥着你刚去深圳时寄的照片,嘴里念叨‘兰儿该回来了’,那照片边角都磨毛了,我给她塞枕头底下的。” 大姑突然站不稳,扶住旁边的老槐树,皮夹克的拉链“咔”地崩开个口子。她从包里掏出个皱巴巴的旧信封,是当年奶奶寄给她的,地址写错了,上个月收拾旧行李箱才翻出来,里面说那半亩地底下埋着她攒的鸡蛋钱,还有一沓她小时候画的小人书。“我不是来抢地的,”她声音发颤,“我就是想把那些东西挖出来……我没脸见我娘。” 我爹从树后面走出来,手里抱着个灰布包:“挖出来大半年了,一直给你留着。你娘说,不管你混得咋样,这都是你的念想。”大姑蹲在地上,眼泪砸在新土上,砸出一个个小坑。她带来的律师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溜了,轿车停在老槐树下,泥点子被风吹得干成了白印。 后来她没提地的事,给村小学捐了两台新电脑,当天就开车回深圳了。今年清明她又来了,没开那辆黑轿车,坐的绿皮火车,拎着个布袋子,给奶奶坟头栽了两棵松树。风一吹,松针晃得厉害,像奶奶当年坐在炕沿上,摸我头时轻轻晃的手。
广州海珠的桥洞下,竟藏着一个让人心揪的家!几块破雨布遮风挡雨,没水没电没门窗,2
【1评论】【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