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陈寅恪落难时,中大“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校内都是他的大字报。但蹊跷在于,陈的友人与学生,竟没一个跟着起哄的。这个现象很特殊。钱锺书这般无世无争的隐士,当年在社科院陷入困境时,照样有不少“熟人”乃至“高足”落井下石,无非雨过天晴不去计较罢了。 1958年,陈寅恪在中大迎来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这位史学界的顶尖人物,平日里低调治学,却因学术地位和历史背景,成了批判的对象。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标语喊得震天响,“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字面刺眼,气氛压抑。然而,有个现象让人摸不着头脑:陈寅恪的友人和学生,竟然没一个跳出来跟着起哄,甚至有人宁可搭上前途,也不愿落井下石。 这事儿跟钱锺书在社科院的遭遇一比,简直天壤之别。钱锺书那么低调的一个人,照样被“熟人”和“高足”批得体无完肤,事后却一笑了之。陈寅恪到底有啥不一样?他的友人和学生为啥这么铁?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 要弄明白这事儿,先得说说陈寅恪是个啥样的人。他1890年出生在江西修水,家里是书香门第,爷爷陈宝箴是晚清维新派的大佬,爹陈三立是清末有名的诗人。这背景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底子。他从小就聪明得不行,精通多国语言,古今典籍随便翻。1902年,他跟着哥哥去了日本,开始闯荡海外。1909年考进德国柏林大学,拜在汉学大师钢和泰门下。1918年又跑去美国哈佛大学钻研东方语言和历史,1921年再到巴黎大学学蒙古语和突厥语。1925年回国后,他进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跟梁启超、王国维这些大牛一起教书。他的研究领域宽得吓人,尤其在中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制度上,成果一个接一个,连《资治通鉴》都被他考证得服服帖帖。 陈寅恪不光学问大,治学态度更是严谨到骨子里。他能直接啃原始文献,考证功夫一流,提出的“诗史互证”方法,至今都是史学界的宝贝。晚年写的《柳如是别传》,考据扎实又满是人文关怀,简直是传世之作。学界都叫他“教授的教授”,地位高得没法说。可他这人低调得很,没啥架子,跟学生聊学术耐心得不行,友人和学生像梁方仲、刘节、季羡林这些人,对他都是又敬又感激。 1958年,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浪潮,陈寅恪自然逃不掉。中大的批判是从郭沫若的一封公开信开始的。郭在信里喊话北大历史系师生,说别把陈寅恪当神,资料上超过他就行。话说得客气,可意思很明白:陈寅恪不是碰不得。中大这边立马跟上,校内大字报满天飞,教学楼、宿舍区,连树上都贴满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的标语。历史系办公室里,有人忙着写批判稿,有人嚷着要“揭露”陈寅恪的“问题”,热闹得不行。 可就在这乱哄哄的场面里,陈寅恪的友人和学生愣是没动静。他们要么不吭声,要么敷衍两句,就是不参与。校方一看这不行,得多找些重量级人物下手,就盯上了陈寅恪在文史两系的教授朋友和老学生。刘节、梁方仲、高华年、赵仲邑、吴宏聪、蒋湘泽,这些都是学界响当当的名字,可没一个买账。刘节被动员时,淡淡地说了句:“陈先生是我老师,我不干这事儿。”梁方仲更直接:“乱拳打不倒老师傅。”连跟陈寅恪关系不太好的容庚,都没吭声。 本地人没戏,校方又找外地的,像季羡林、蒋天枢、姜亮夫、王力、吴晗、夏鼐这些大牛,结果还是一样。季羡林后来回忆,他不反对批判运动,可对着陈寅恪下不去手,动员的纸条攥在手里,最后还是放下了。吴定宇翻了当年的批判文章,发现没一个跟陈寅恪关系近的重磅学者参与。他们可能在别的场合批判过别人,但对着陈寅恪,硬是没动。 唯一有点动静的是周一良。他跟陈家四代交好,是陈寅恪看重的学生,专攻魏晋南北朝史。可在压力下,他在北大贴了篇“反思”文章,说陈寅恪研究中古史是嫌先秦史料少、宋代史料多,还批评这是“个人成名”的私心。这话看着像批判,其实没啥分量,对陈寅恪伤不了根毛。可对周一良自己,这成了心病,后来他还专门写了篇《向陈先生请罪》,说自己当年没办法。 再看看钱锺书。同样是大牛,《围城》写得天下皆知,平时低调得不行。可他在社科院陷入困境时,“熟人”和“高足”没少下黑手。有人为了自保,有人为了表忠心,批判文章写得飞起,事后却跟没事人似的。这种事儿在那年头不新鲜,很多学者都碰到过,身边人翻脸比翻书还快。可陈寅恪这边,友人和学生愣是顶住了压力,没一个跟着起哄。这差别,实在太明显。 陈寅恪的友人和学生为啥这么铁?有几个原因。第一,他的学问和为人太让人服气了。他不光教书育人,还拿自己的治学态度影响了大家。学生们知道,陈寅恪的成果不是吹出来的,是真功夫。第二,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多少还有点底线和良知,觉得学术得讲独立,不能被政治牵着走。陈寅恪的友人和学生就带着这股劲儿,宁可沉默也不瞎掺和。第三,他们跟陈寅恪不光是师生关系,还是朋友关系。这种情分,让他们没法对陈寅恪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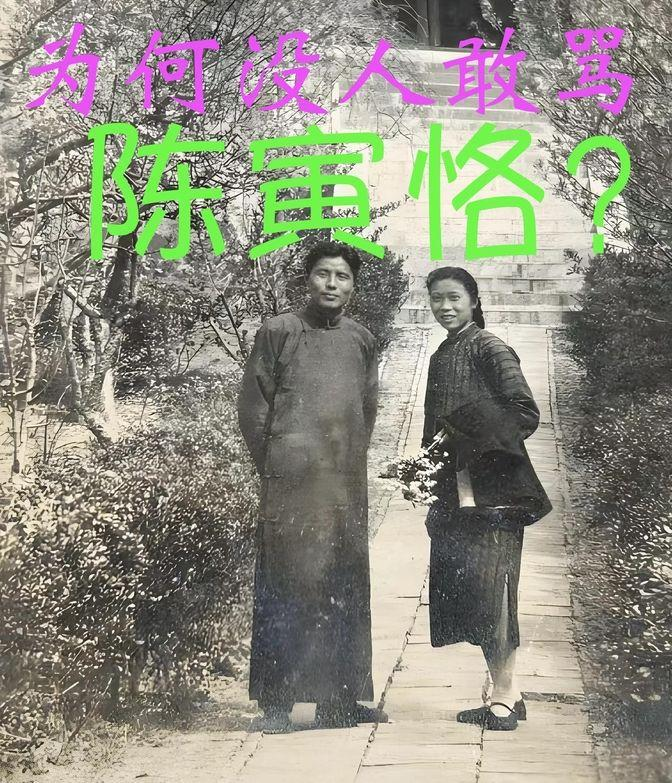

用户10xxx90
人格魅力
五月天的葡萄树
倒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