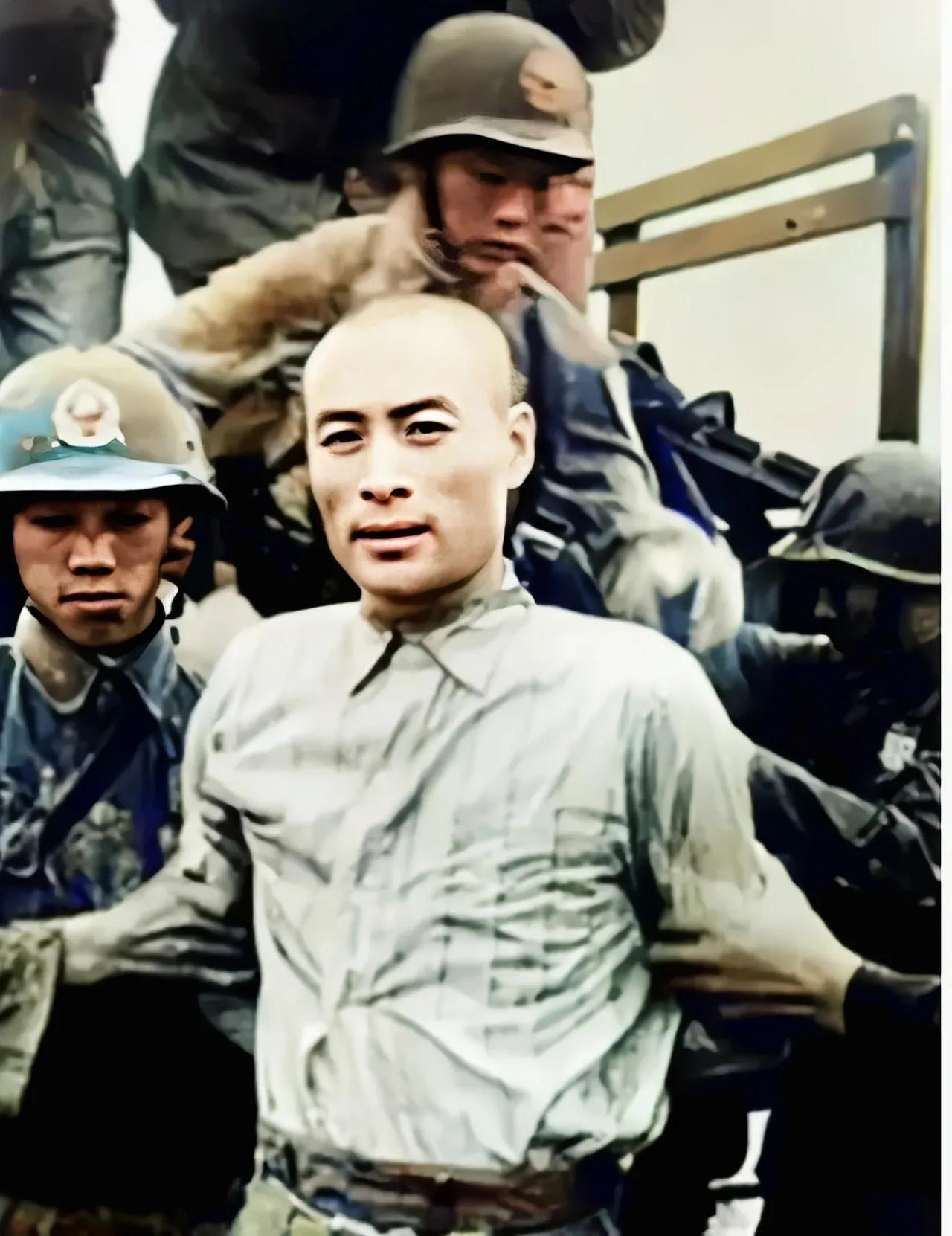1903年,八名“上海名妓”的一张留影,不知道是因为相机反光的原因,还是因为她们在脸上抹了什么粉,感觉她们的整张脸都像石膏板做成的一样,显得特别的呆板,似乎是木头人定在了那,看起来苦大仇深,用“歪瓜裂枣”来形容,估计也一点都不为过。 首先得赖那老掉牙的照相机。19世纪末,照相馆在上海算是个顶时髦的新鲜玩意儿。可那时候的拍照技术,跟咱们现在手机随手一拍可完全是两码事。曝光时间特别长,没个几十秒甚至几分钟下不来。让所以,照片上的人看起来像木头人,真不全是她们的锅。 再说那张“石膏板”一样的脸。这就要说到当时的化妆术了。那年头,粉底可不是什么轻薄透气的玩意儿,很多都是含铅含汞的,死白死白的。往脸上一抹,遮盖一切瑕疵,也遮盖了一切表情。在当时昏黄的灯光下,这种妆容或许能显得人很“白皙”,但在照相机那无情的镜头下,就成了咱们今天看到的面具脸。 所以啊,咱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轻易评判一张1903年的照片。这张照片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别被表象骗了。她们之所以看起来“苦大仇深”,很可能只是因为拍照的技术限制,加上当时独特的审美妆容。 聊完照片本身,咱们再往深了挖。这些女人,到底凭什么在上海滩立足?单靠脸吗?那肯定不行。 在晚清的上海,妓女这个行当,也分三六九等。最高等的叫“书寓”,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这些女子大多来自苏州,能弹会唱,懂点诗词,有的甚至会画画,堪称“女校书”。比如有个叫李萍香的,资料说她“家世簪缨”,书香门第出身,自己也是“工吟咏,擅书画”,可惜后来被坏人所骗,才堕入风尘。她们卖的,更多是“艺”,是那种文人雅士追求的调调。客人在堂子里摆酒,请她们来,往往是“拨弦清唱”,助助雅兴。这跟咱们想象中的青楼,完全是两个概念。 再下一等,就是“长三”,也属于高级妓女。她们的场子叫“长三堂子”,是当时重要的社交场所。那会儿的生意人、社会名流谈生意、搞交际,很多时候都选在这种地方。你想想,能在这种场合游刃有余的女人,能是普通角色吗?她们不仅要有才艺,更得有眼力见儿,懂人情世故,情商个顶个的高。 所以说,这些所谓的“名妓”,其实是那个时代上海滩的社交名媛和时尚先锋。她们的价值,远不止于皮囊。 说到时尚,那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当时上海滩的穿衣潮流是怎么来的?有句话说得特别到位:男人看女人,女人看妓女。没错,她们就是当时行走的“时尚杂志”。什么新发型、新首饰、新衣料,往往都是先从她们身上流行开来。 她们还是最早拥抱摄影术的那批人。当大部分良家妇女还觉得照相是“勾魂摄魄”的玩意儿时,她们已经大大方方地走进照相馆,留下自己的倩影了。这当然有商业上的考虑,照片印在一种叫“局票”的单子上,方便客人点名,相当于最早的“明星宣传照”。但不管怎么说,她们确实引领了这股风潮。后来,去照相馆拍照,才慢慢成了普通市民也热衷的活动。 所以你看,这张照片里的“木头人”,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一个个鲜活的、引领潮流的“弄潮儿”。她们的生活,远比一张静态的照片要丰富和复杂得多。 当然,风光的背后,也少不了辛酸和狗血。 那个时代的小报,跟咱们现在的娱乐八卦号也差不多,最喜欢报道这些名妓的花边新闻。比如当时有个花界“四大金刚”之一,花名叫林黛玉的,就和一个唱戏的武生赵小廉好上了。俩人偷偷在张园约会,结果被巡捕给当场逮住,闹得满城风雨。这种“娼优相狎”的故事,在当时可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顶级谈资。 还有些故事,就没那么轻松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李萍香,身世可怜。也有像赛金花那样,命运跟过山车似的,十几岁就嫁给高官,后来又流落风尘,一生充满传奇,也充满无奈。她们看似在名利场里呼风唤雨,但终究是漂泊的浮萍,自己的命运,多半由不得自己做主。那一张张看似呆板的面孔背后,藏着多少身不由己和言不由衷,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如今看着这些泛黄的影像,心里难免会生出很多感慨。 回过头再看那张“八大名妓”的照片,我不再觉得她们“歪瓜裂枣”,也不再觉得她们“呆板”。反而能从那一张张平静得有些过分的面孔下,读出一种无声的力量。那是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里,一群特殊女性努力活出自我、甚至引领潮流的证明。她们的故事,远比小说要精彩,也远比历史书上那几行冷冰冰的文字,要有血有肉得多。 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此。它总是在不经意间,用一张模糊不清的老照片,向我们抛出一个又一个谜题。而我们,就像侦探一样,通过蛛丝马迹,去努力还原一个更接近真实的过去。这个过程,本身就比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要有意思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