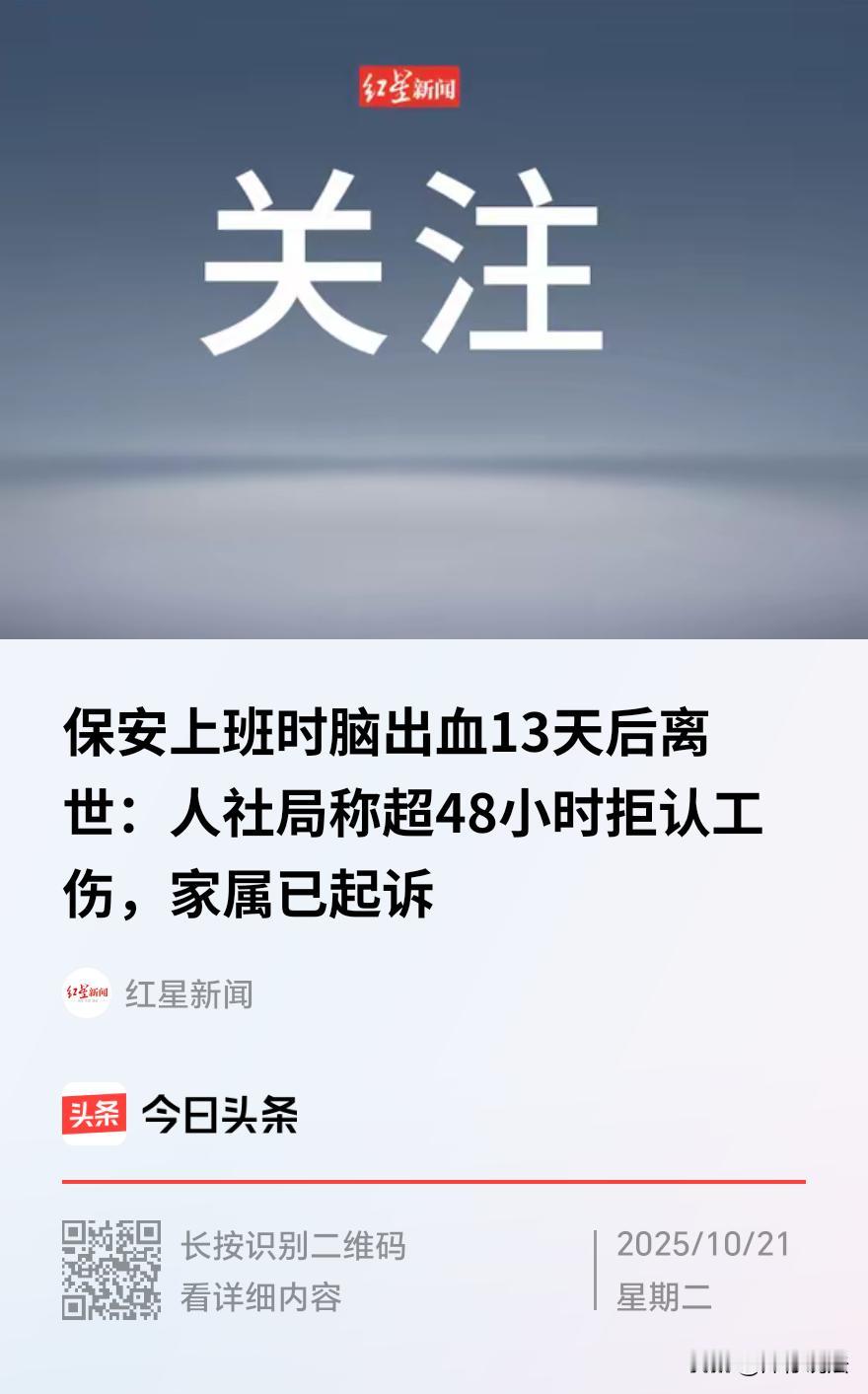广东东莞,一51岁保安在工业园岗亭执勤时突发脑出血,深度昏迷,医生在48小时内明确告知家属,他已处于“脑死亡”状态,救治无望。然而,亲情的本能让家人无法放弃,他们选择继续用呼吸机维持着他的生命,直到13天后,保安的心脏最终停止跳动,死亡证明上死亡时间写的是13天后的时间。事后,公司为保安申请工伤认定,但人社局以“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为由拒绝。家属不服,认为保安在48小时内已实际脑死亡,如为了工伤认定赔偿在48小时内主动放弃抢救有违公序良俗,遂将人社局告上法庭。 据悉,2024年,蒋本武(化名)在一家豪丰公司(化名)担任保安,年纪才51岁,平时负责大门口的岗亭值班。 2024年11月1日,蒋本武一大早像往常一样在岗亭执勤。8点30分左右,他突然感到头晕,随后栽倒在地。 工友刘杰明(化名)赶紧冲过去,发现蒋本武已经不省人事,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救护车很快赶到,将他送往医院,急诊记录显示,蒋本武处于“深昏迷状态”,双侧瞳孔放大,……存在脑出血,出血量达62毫升,并破入脑室系统。 医生当场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建议转往上级医院。 当天11点45分,蒋本武被转入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转院途中,医生通过电话告知家属,蒋本武的病情极其危重,已处于濒死状态,穿刺检查都无反应。 下午1点35分,医院的会诊记录单上写道:“脑室积血、脑室铸形,随时有心跳骤停可能。” 当晚10点,主治医生召集家属谈话,明确表示蒋本武的脑干损伤不可逆,治疗已无意义,继续抢救可能只是延长痛苦。 蒋明和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如遭雷击。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坚持要求医院尽力救治。 家属的坚持,让医院继续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和药物治疗,维持蒋本武的生命体征。 11月2日下午2点,医院再次告知家属,蒋本武已处于“脑死亡”状态,建议放弃治疗,并询问是否考虑遗体捐献。 家属仍不愿接受,请求继续治疗,在接下来的12天里,蒋本武一直躺在急诊ICU病房,依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生命。 每天,医疗费用高达数千元,很快耗尽了家里的积蓄。 11月13日,家属最终决定办理出院手续,租用带呼吸机的救护车,将蒋本武送回湖北老家,希望他能“落叶归根”。 11月14日上午10点,救护车抵达老家,当地卫生院因设备限制,无法立即衔接呼吸机。在撤下设备的短暂过程中,蒋本武的心脏于10点18分停止跳动。 卫生院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亡原因为“脑出血并发脑疝”,死亡时间为11月14日10点18分。 蒋本武去世后,豪丰公司于11月6日向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公司提供了考勤记录、岗亭监控视频和工友证言,证明蒋本武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然而,11月14日,人社局出具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理由是蒋本武“非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不符合规定情形。 家属对此决定无法接受,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人社局列为被告,豪丰公司作为第三人。 目前,案件诉讼于2025年10月9日开庭,尚未宣判。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呢? 《民法典》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的死亡时间,以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本案中,蒋本武的死亡证明记载时间为11月14日,远超48小时。 人社局严格依照既有死亡证明和传统的死亡标准进行认定,在行政程序的框架内,似乎做到了“有法可依”。 在司法实务中,死亡标准有两个,分别是“脑死亡”和“心肺死亡”,而以“心肺死亡”标准居多。 不过,当法律规定存在模糊或空白时,应遵循“有利于劳动者”的解释原则。工伤保险制度根本立法目的是保障因工作遭受伤害或疾病的劳动者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具有明显的倾斜保护属性。 在死亡标准存在争议时,作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更符合立法本意。 从医院的病程记录、病危通知书以及医生与家属的谈话内容等证据,均强有力地证明了蒋本武在48小时内出现了“脑死亡”状态。 从有利于劳动者角度,蒋本武的死亡有机会被认定为工伤。 此外,《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正如家属所说,若要求家属为了工伤认定赔偿,48小时内主动放弃抢救,既有悖伦 理道 德,也不符合公序良俗与常理。 而支持工伤认定,是对亲情和公序良俗的捍卫,能够向社会传递正向价值,避免法律规则成为伦理选择的“刽子手”。 有人说,当在48小时内,患者出现脑死亡,其后的生命维持纯属基于伦 理情感的医疗干预时,其死亡时间应追溯至脑死亡发生之时,不受“48小时”的刚性限制,这样才更加合理。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