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学的诞生及其创始者岸俊男者岸俊男,是日本京都大学研究日本史的权威,岸俊男晚年提出平城京建设受洛阳影响而非长安,还认为日本诸多文化都源自洛阳传播,而当时学界普遍将日本古都文化源头归为长安 。 由此,他提出了“洛阳学”,其核心是,用不同视角,新的观点,多维度的研究洛阳历史,重塑历史叙述。 一个日本史研究者,把触角伸到了洛阳,重新用不同视角重塑洛阳历史的“洛阳学”诞生了。 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看他突发灵感的提出“洛阳学”的依据, 晚年的他认为, 1、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的城市建设布局,受洛阳影响而非长安。 2、日本的诸多文化,都源自洛阳传播,而不是学界普遍认为的,日本古都文化源头归属为长安 。 “洛阳学”,正是他要改变日本文化受长安影响的普遍共识,独树一帜的提出,洛阳才是日本文化的传播者。 那么,岸俊男提出的以上两点,符合历史事实吗? 首先看第一条,平城京城今奈良是受洛阳城市影响,而不是受长安城的影响。 那么,奈良的中轴线从哪里来的? 是洛阳吗? 它的中轴线依然称,朱雀街。 为何不称定鼎门街呢? 难道中轴线不受长安影响么? 可见其为了改变历史认同,以洛阳为突破口,把日本文化的源泉归到洛阳,而不是长安。 从而引起人们对历史的争议。 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周秦汉唐为荣耀的长安,产生分歧,撕裂民族的文化认同感。 抛出,用不同观点,多视角的研究洛阳历史,重塑洛阳的历史地位的洛阳学。 颠覆长安对日本的影响力,让洛阳成为 文化传播者的核心。 从而来否定长安的历史地位。 他的这一核心论点,随未获得日本主流学界认可,但他联合中国学者,一起在日本大学共同组建了“洛阳学”。 不得不说他很懂中国人情世故,“洛阳学”要拉上中国学者,好让他的核心主张,有中国人为他发声。 下面具体论述,驳斥他创立洛阳学的灵感来源, 岸俊男提出,“日本文化受洛阳影响而非长安”的观点,既与都城规划的考古实证相悖,也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史料记载不符,以下从都城建设、文化传播、文物佐证三方面逐一驳斥: 1. 平城京规划核心照搬长安,而非以洛阳为主 :平城京的核心布局与长安高度契合。它将宫城“大内里”置于城北正中,宫前朱雀大路作为中轴线贯穿南北,把城区划分为左京和右京,两侧规划棋盘式坊市,还设置东市、西市,这和唐长安城宫城居北、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坊市对称的核心规划如出一辙。日本奈良县政府官网也明确记载平城京是模仿唐长安城而建。而岸俊男刻意忽视这些核心特征,仅以坊为正方形等个别细节对标洛阳,显然是片面取舍证据。 2. 遣唐使交流重心在长安,文化传播主线指向长安 :唐朝长安作为都城,是当时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日本遣唐使的核心目的地多为长安。众多日本留学生、僧人在长安求学修行,比如平城京药师寺相关的佛足石复刻品,就是日本留学生在长安临摹后带回安置的 。且平城京后期模仿长安大明宫鳞德殿建造楼阁用于宴会,这种宫殿功能与形制的借鉴,正是长安文化深度影响的体现,绝非洛阳文化主导传播的结果。 3. 器物与制度层面,长安影响的痕迹不可磨灭 :一方面,平城京建筑的绿釉瓦技术、奈良三彩的烧制,均是对长安相关工艺的吸收改造,这是日本学界也认可的技术传承脉络 ;另一方面,平城京的朝堂朝会制度、官员上朝退朝的时间规范等,都参照了长安的唐代官制律令。即便正仓院部分文物与洛阳器物有相似性,也仅能说明两京文化共同对外传播,而非洛阳单独主导,岸俊男将这种共同影响歪曲为“非长安”,完全违背了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 此外,岸俊男还混淆了不同时期的都城体系,他将平城京与魏晋南北朝洛阳城的零星相似性,当成唐代洛阳对日本文化的主导影响。事实上,主流学界早已达成共识,平城京及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化,是兼取唐长安、洛阳两地之长形成的,岸俊男的观点本质是片面截取个别文化碎片得出的结论,根本无法支撑“日本文化受洛阳影响而非长安”的核心论点。 岸俊男的洛阳学灵感,像极了今天的丝绸之路双起点。是不顾历史事实的重塑洛阳历史。将丝绸之路起点的整体性,割裂为东汉,西汉叙述丝绸之路起点,从而得出两个起点 。挑起了国人对历史起点的纷争。 洛阳学,妙就妙在,用不同视角,多维度重塑历史。让统一的历史认同出现裂痕,引起文化纷争。 为什么不能以国家历史教科书为准绳呢? 不同视野,多维度研究洛阳,重塑历史。不是让你毫无底线。应当是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历史教科书为准绳,再去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洛阳历史,让洛阳历史的闪光点充分展现。而不是触碰底线的夸大历史叙事。 岸俊男正将自己错误的历史价值观,通过洛阳学传播。 一个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并抛出新视角,多维度,重塑历史,不得不引起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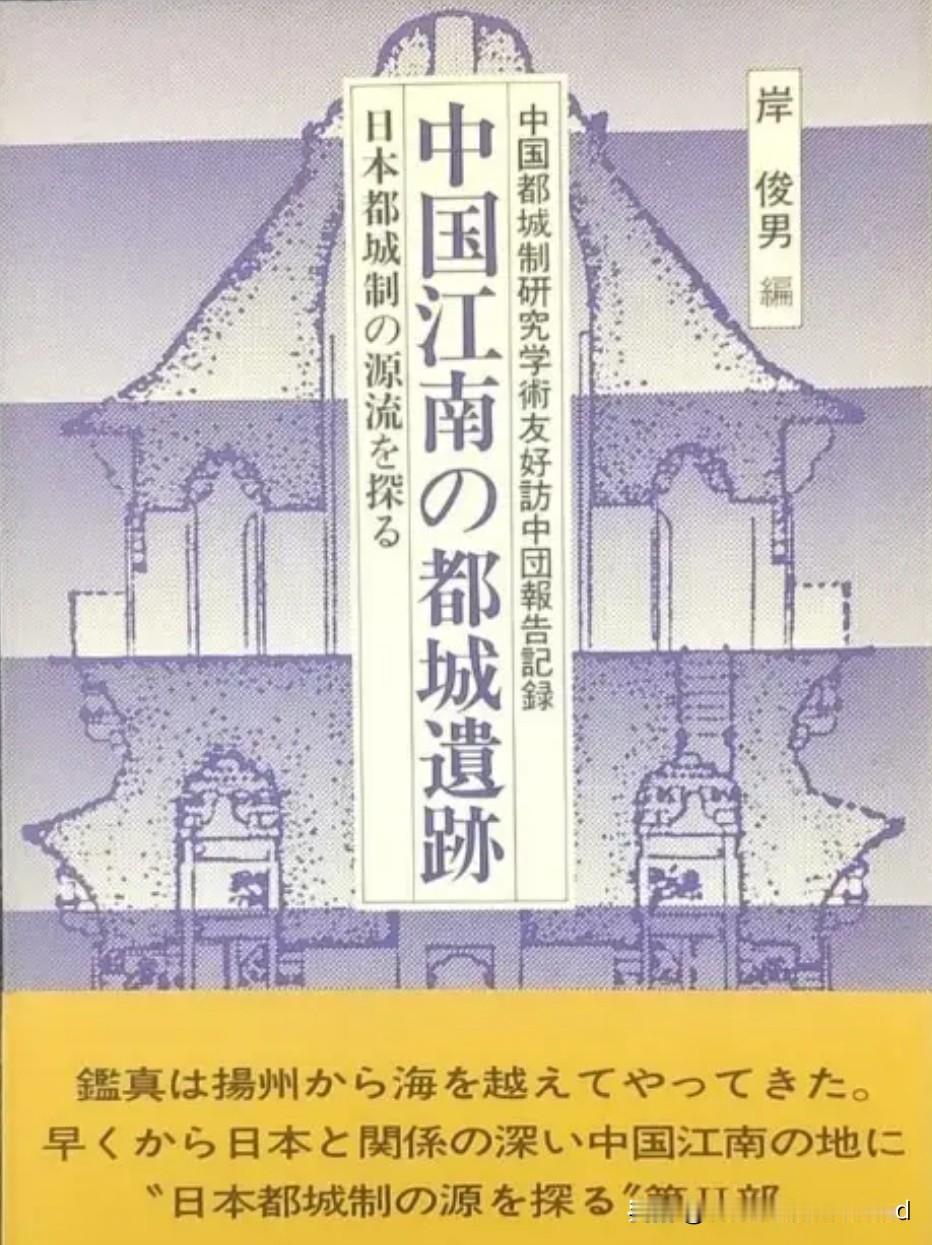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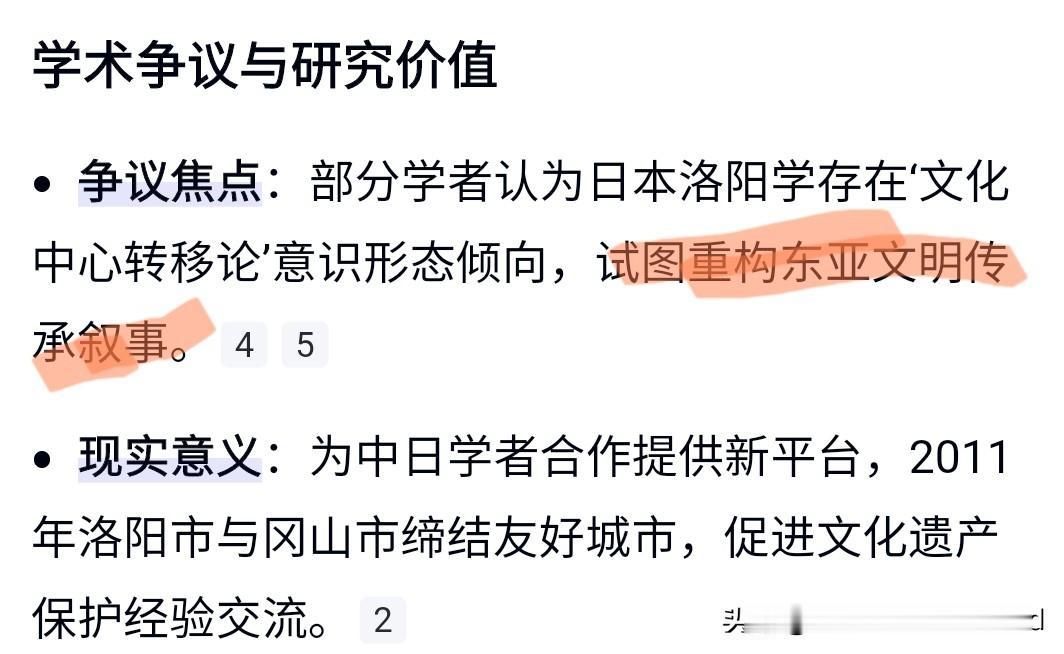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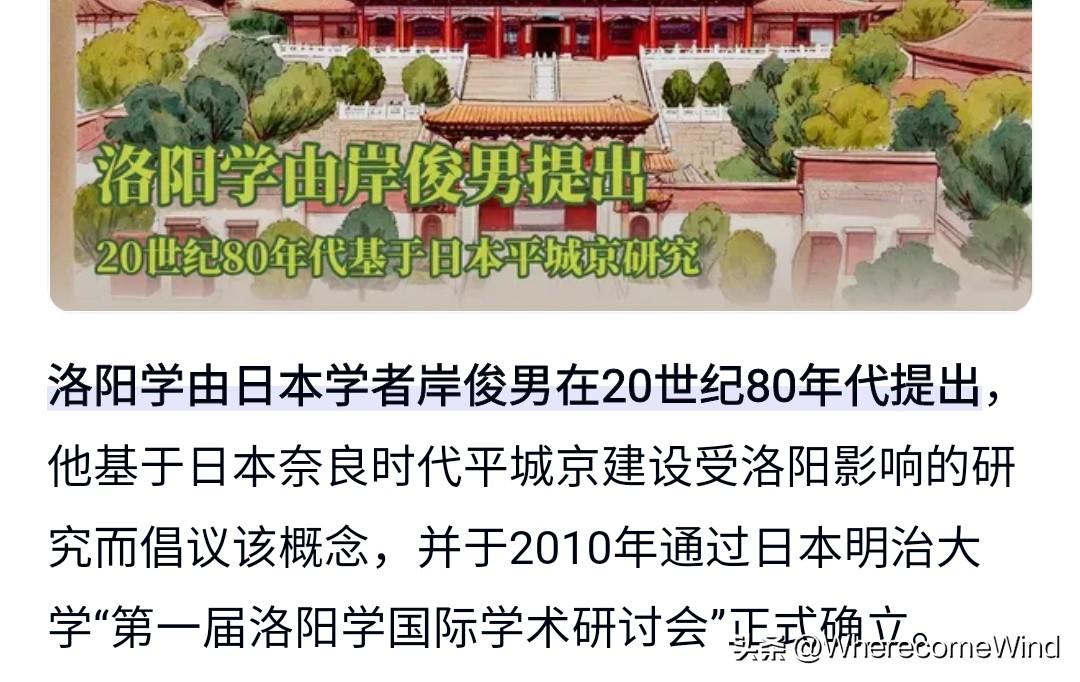

xbyf
阳阳和长安争丝绸之路,让日本人看到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