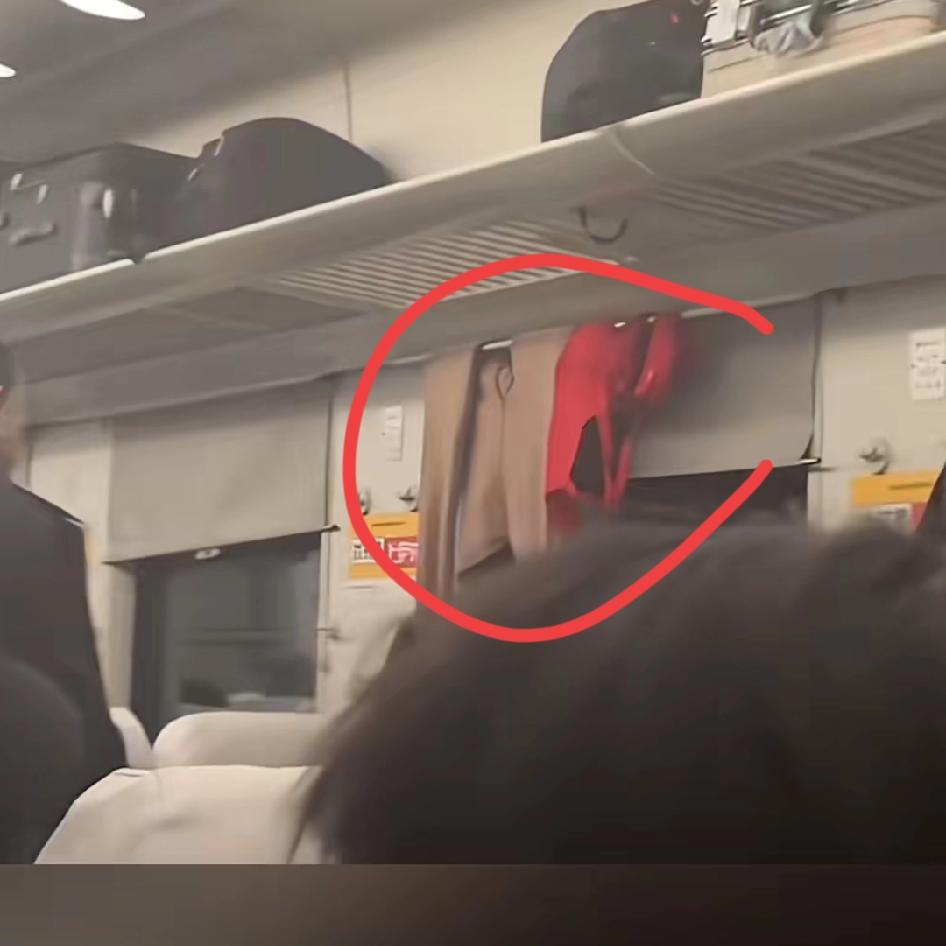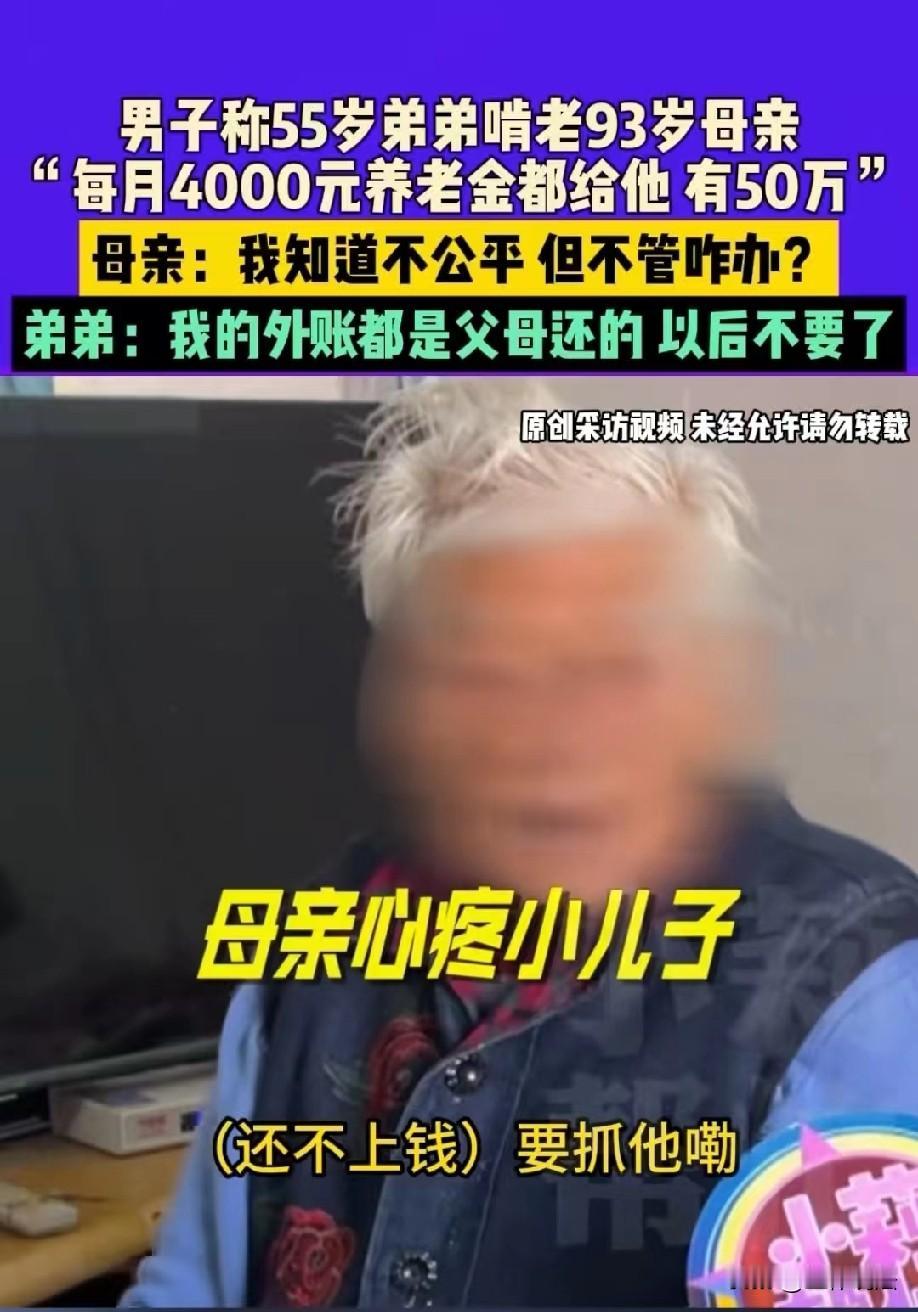突然很想念独居在家的老母亲,于是一人一包往家赶,本想着给母亲一个惊喜,火车快到站的时候才给她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响了三声才被接起,那头传来母亲带着点沙哑的声音,还夹杂着电视里戏曲的背景音。 独居的老母亲总说自己过得好,电话里永远是“不用惦记”,可挂了视频我总看见她沙发扶手上搭着没织完的毛线——针脚歪歪扭扭,像她没说出口的话。 那天加班到八点,电脑屏保突然跳出去年给她拍的照片,她站在小区那棵老槐树下笑,假牙没戴好,嘴角歪着——突然就想家了。 抓起背包就往车站跑,票是站票,车厢连接处风灌进来,裹着泡面味和行李箱滚轮的咕噜声,我靠在车门上数隧道,一个接一个,像数她独居的那些夜晚。 快到站时才敢拨号,怕她提前等在站台——她总这样,知道我要回,能从下午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楼下,直等到路灯亮透,这次没提前说,她该不会还在看电视吧? 电话响了三声,比平时多一声。 “喂?”她声音有点哑,背景音是咿咿呀呀的京剧,《锁麟囊》,她最爱的那段,“这时候打电话,是下班了?” “妈,我快到北站了。”我故意说得轻描淡写,等着听她惊喜的尖叫——可电话那头静了静,只有胡琴声还在飘,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响动,像有人急着起身,碰倒了什么。 出站时远远看见她,还是那件藏青色棉袄,袖口磨得起了球,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风把她头发吹得乱蓬蓬的,她没往出站口看,倒盯着手机屏幕,手指在上面戳戳点点——后来才知道,她把我的车次设了特别提醒,从下午三点就开始刷新“列车正晚点”。 我走过去拍她肩膀,她猛地回头,眼睛亮得吓人,手里的塑料袋掉在地上,滚出两个还热乎的茶叶蛋。 “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她声音更哑了,却伸手来接我背包,指腹蹭过我手腕,糙得像砂纸,“我以为你得半夜才到,锅里还给你留着粥呢。” 电话里的戏曲声还在我脑子里转,原来她不是在悠闲看电视,是把音量调大了——怕听不见手机响,又怕声音太小,显得自己太盼着我回来,让我操心。 她总说“不用惦记”,是怕我知道她把降压药掰成半片吃,怕我看见她冰箱里只有咸菜和馒头,更怕我知道,每个想我的晚上,她都抱着我的旧照片,在沙发上坐到天亮——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全藏在歪歪扭扭的毛线针脚里,在热乎的茶叶蛋里,在哑着嗓子却不肯挂的电话里。 那天晚上,我把她没织完的毛线拿过来,教她怎么收针,她眼睛不好,我就握着她的手慢慢绕;后来每个周末,我都往家跑,哪怕只待两小时——原来所谓惊喜,从来不是突然出现,而是让她知道,她等的人,也在拼命奔向她。 现在想起那天火车上的风,裹着泡面味和隧道的黑,却吹得人心里发暖——因为我知道,隧道那头,总有个人,攥着热乎的茶叶蛋,在路灯下等我,像等了一辈子那么久。
突然很想念独居在家的老母亲,于是一人一包往家赶,本想着给母亲一个惊喜,火车快到站
嘉虹星星
2025-12-15 16:07:06
0
阅读: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