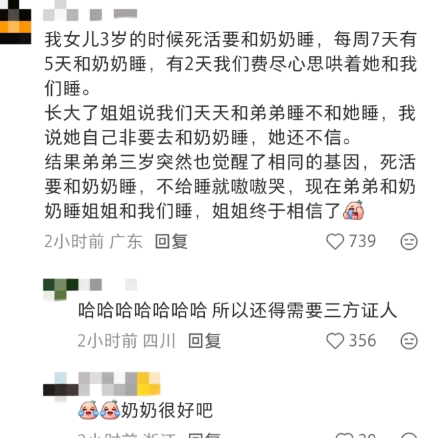以前的农村讲究人情,今天你帮我收稻谷,明天我帮你修房子,相互欠这些人情。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找别人干活,没有人情,直接谈钱。想要借钱,就必须打欠条算利息。大家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其实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我家墙上挂着把旧镰刀,木柄被爷爷的手磨得发亮,那是三十年前的物件了。 那时候村里谁家收稻谷,不用喊,天蒙蒙亮田埂上就站满了人。我蹲在田边啃红薯,看爷爷挥着这把镰刀,身后跟着王伯、李婶,割倒的稻穗在晨露里堆成小山。收完了,奶奶端出腌菜稀饭,大家蹲在田埂上呼噜噜喝,王伯抹嘴说:“明天你家帮我修下牛棚啊。”爷爷应得脆:“没问题,带把锤子来就行。” 前几天猪圈漏雨,我望着墙皮剥落的屋顶发呆,突然想起王伯当年帮我家盖房的样子——他踩着梯子递瓦,我爸在下边接,俩人连句“谢”都没有,就像左右手配合。现在王伯老了,他儿子小辉在镇上开装修队,我揣着两盒烟去找他,刚开口说“小辉,叔家猪圈……”他就掏出手机:“叔你量下尺寸,我算算工时费,材料你自己买还是我帮你带?” 我捏着烟盒的手紧了紧,烟盒皱成一团——这场景怎么跟记忆里不一样了?小时候他跟着王伯来我家,我妈塞给他个煮鸡蛋,他剥开壳先递到我嘴边,现在怎么说起钱来了? “咋还说钱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涩,“当年你爸帮我家盖房,可没要一分钱。” 小辉挠挠头,刘海下的眼睛亮亮的:“叔,那时候是那时候,现在我这队里有工人要开工资,我要是给你免了,回头他们跟我算不清,队伍就散了——再说,亲兄弟明算账,免得以后为这点事心里隔应,你说是不?” 他说得实在,我却想起去年冬天,他爸半夜突发心梗,是我骑着电动三轮把老人往镇医院送,挂号、垫付医药费跑前跑后,天亮时小辉从外地赶回来,红着眼圈要转钱给我,我按住他手机:“跟你爸当年帮我家一样,提钱就见外了。”那天他没转成,今天算工时费,倒像把那份情换成了明晃晃的数字,摆在我面前。 后来猪圈修好了,请小辉吃饭的时候他非要买单,说:“叔,你别觉得我生分。现在村里人大多在外头打工,一年到头碰不了几次面,以前天天见,可以慢慢还人情,现在见一面难,欠着情不还,心里比欠钱还慌——倒不如算清楚,下次你家再有啥事,我还能踏踏实实地来,不用琢磨‘上次欠他的还清没’。” 回家的路上,风从田埂吹过,稻浪沙沙响,跟三十年前一样。我摸出手机,翻出小辉发来的说工时费明细截图——其实他把零头抹了,还备注着一句小字:“叔你帮我爸那次,抵了。”原来他没忘,只是换了种方式记着。 墙上的旧镰刀还挂着亮堂堂地,旁边压着张纸条,是小辉写的工时费欠条,墨迹新鲜。小时候觉得人情像这镰刀木柄上的包浆得靠日子慢慢磨养着;现在才明白日子快了磨不住包浆,那就换成欠条上实实在在的数字,数字会过期,但藏在数字背后的惦记,说不定比包浆更经得住晒。 只是不知道下次村里再有谁家收稻谷,田埂上还会不会站满不用喊就来的人,或者,会不会有人像小辉这样,算清了工时费,却悄悄在田埂边给帮忙递袋子的老人塞个热乎馒头——毕竟日子再快,人心底那点暖不该凉透,对吧? 现在我把那把旧镰刀取下来擦了擦,又挂回墙上,旁边摆着小辉的欠条——旧的没丢,新的也来了,或许人情不是淡了,是换了件衣裳,继续陪着日子往前走呢。
外婆很聪明,这六个子女里,她偏偏认准了最闷葫芦、性子最温吞的三舅养老,一头扎进了
【3评论】【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