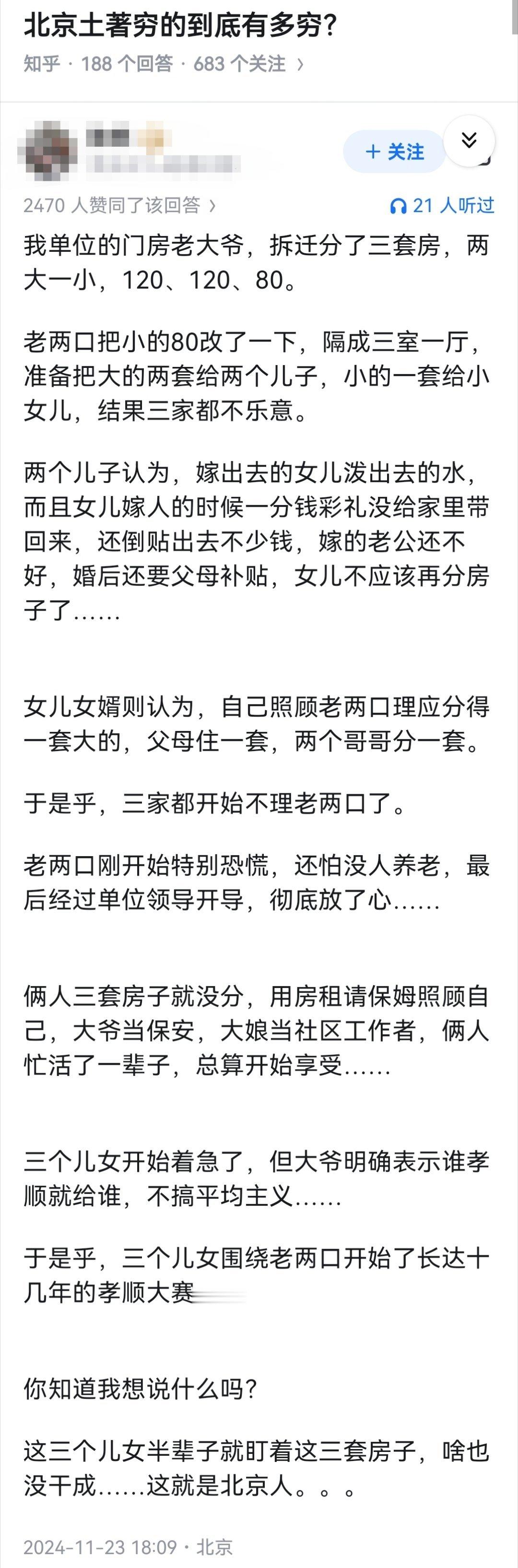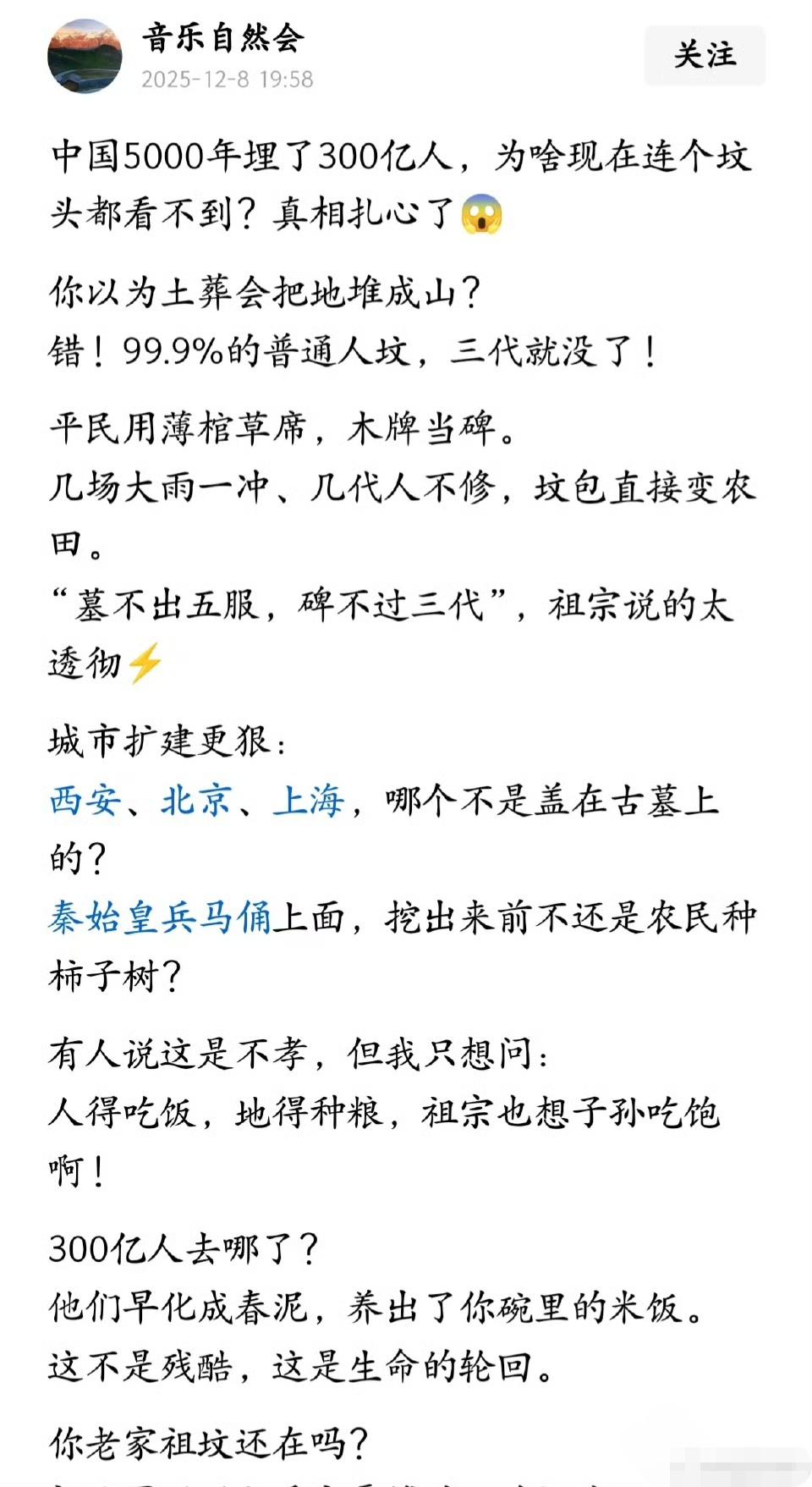1980年的一天,孙健正在外地的一家煤矿视察,这时秘书急匆匆地交给他一份加急电报,电报要求他尽快赶回北京。 电报在孙健手中微微发颤,黑色的铅字像一个个沉甸甸的问号。 他刚结束井下巡查,安全帽上还沾着煤尘,矿灯的光晕在电报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 这封来自北京的加急电报,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头,在他心里激起层层涟漪。 返京后的谈话室里,老式吊扇慢悠悠转着。 组织上提出的干部调整方案摆在桌上,孙健的手指在"自愿申请"四个字上停顿片刻,笔尖划过纸面时发出沙沙声响。 那个年代,干部从领导岗位转到基层并非易事,不少人私下劝他再考虑,可他望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想起煤矿井下工人们黝黑的脸庞,最终还是在申请上签下了名字。 天津内燃机厂的铁门锈迹斑斑,孙健第一天报到时,传达室大爷上下打量他许久。 车间里机油味混杂着汗水味,车床轰鸣声震得人耳膜发颤。 他主动要求从最基础的装配工做起,蓝色工装很快沾满油污,手掌磨出的茧子比在煤矿时还要厚。 起初有人背后议论"大领导来体验生活",可当看到他蹲在地上用扳手拧螺丝一蹲就是两小时,这些声音渐渐没了踪影。 食堂的长条凳成了他的临时办公桌,午饭常常是半个馒头就着咸菜。 有次技术员们为图纸争得面红耳赤,孙健默默把图纸铺在饭桌上,用沾着机油的手指点出关键尺寸。 "这里的公差配合得改改,"他声音不大却很笃定,"咱们的零件得经得起市场敲敲打打。 "那个月,车间的废品率降了近三成。 职工宿舍的墙皮有些剥落,孙健的行李简单得像个探亲的工人。 隔壁老钳工发现,这位"新来的老孙"总在下班后留在车间,台灯下画图纸的身影常常映到后半夜。 有回暴雨冲垮了仓库屋顶,他带头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抢搬零件,第二天发烧到39度还咬着牙上了生产线。 厂门口的梧桐树换了四次叶子,车间的机床更新了三代。 曾经亏损的厂子不仅扭亏为盈,产品还卖到了南方几个省。 可孙健的咳嗽声越来越重,起初以为是老慢支,直到那天在调度会上咳出了血。 医院的诊断书下来时,他正盯着新季度的生产计划表,钢笔尖在"合格率100%"那行字上洇出个墨点。 1989年冬天,天津街头飘着小雪。 送葬的队伍从内燃机厂一直排到烈士陵园,不少退休老工人自发举着"老孙我们想你"的纸牌。 灵车上覆盖的党旗在寒风中微微起伏,就像当年他在煤矿井下看到的那盏矿灯,虽然微弱却始终照亮着前方的路。 那封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加急电报,后来被档案馆收藏,泛黄的纸页上,"尽快赶回北京"六个字依然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