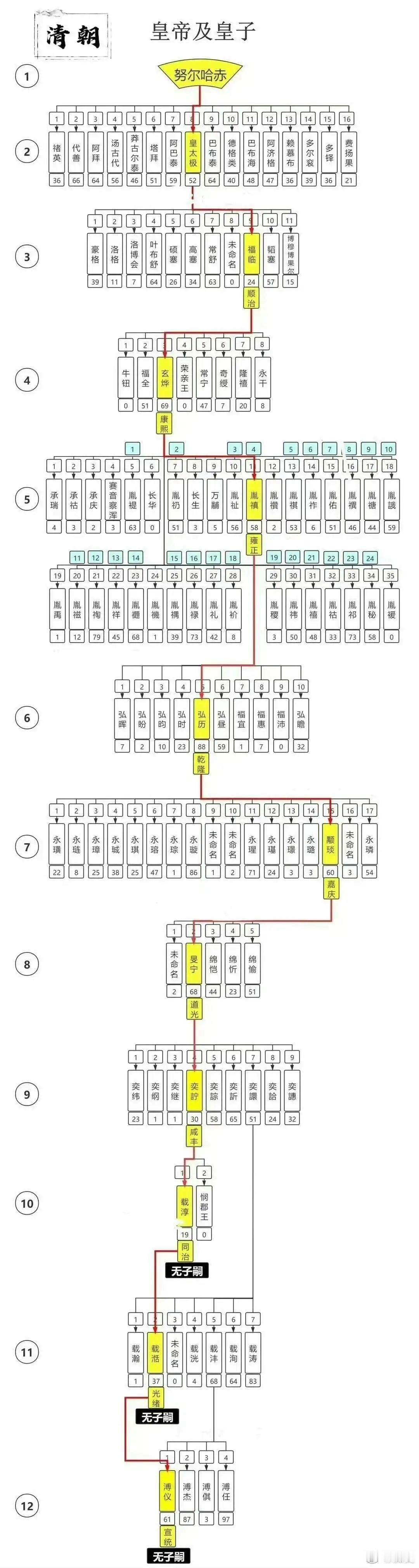77岁的武则天被男宠张昌宗折腾到筋疲力尽,没曾想,当她沉沉睡去之后,张昌宗却偷偷溜去了隔壁偏殿,门一合上,人就凑近那个等着他的女子,低声说了句,歇下了,放心。 偏殿里的沈青萝指尖泛白,攥紧的手帕上半朵寒梅绣得针脚发颤——那是前宰相沈君谅的族徽,八年前因反对武周称帝,沈家满门流放岭南,她以宫女身份入宫,等的就是这一刻。 张昌宗按住她肩头的手带着刻意的温柔,指腹划过领口那排代表局势急缓的暗号针脚。没人知道,这个被武则天唤作“六郎”的俊美男宠,每晚给太后揉肩时都在发抖——他见过薛怀义被挫骨扬灰的灰烬,听过沈南璆暴毙当夜的风声,恩宠这东西,薄得像层窗纸。 龙床上的武则天其实没真睡死。呼吸声里的沉重是真的,眼角皱纹被烛火刻出沟壑也是真的,但枕头底下那本《臣轨》硌着后脑勺——年轻时用来规训百官“事君尽忠”的典籍,如今书页被摩挲得发毛,倒像是在嘲笑她连枕边人都管不住。 昨晚张昌宗故意提起庐陵王在房州种的麦子收成,她看见他眼角瞟向自己的凤印,也看见他转身时袖角沾着的宫外泥土——那是李唐宗室私下联络的信物。她没接话,只是咳嗽了两声,看他慌忙递水的样子,忽然想起当年自己亲手把李显废为庐陵王时,他也是这样跪伏在地,连头都不敢抬。 宫里人都说太后老糊涂了,被两个姓张的兄弟迷得团团转。可谁见过她深夜独坐时,用枯树枝似的手指在沙盘上画“周”字又抹去?或许不是糊涂,是真的累了——处理完突厥的军情,还要应付御史弹劾张氏兄弟的奏章,77岁的身体,早被权力和岁月榨干了最后一丝锐气。 沈青萝望着张昌宗年轻却阴鸷的脸,忽然想起祖母临行前塞给她的话:“宫廷是染缸,要么染黑,要么被吞。”她原本只想给流放岭南的父亲传一句“梅开待雪”的暗号,可现在,张昌宗的计划里不仅有“复唐”,还有“废后立幼”——他想做第二个武则天,而她,不过是他棋盘上那颗刻着“沈”字的卒子。 张昌宗把沈家旧部、李唐宗室都当成筹码,却忘了武则天能坐稳皇位,靠的从来不是恩宠,是杀伐决断。当年她连亲儿子都能废黜,如今怎会看不出他袖口的泥土?只是凤印虽重,握印的手却抖得连奏章都快批不动了——权力的本质是平衡,当她再也无法平衡朝堂各方势力,张氏兄弟的嚣张,不过是权力崩塌前的最后一阵喧嚣。 三天后,张昌宗又在偏殿和沈青萝密谋时,武则天突然出现在门口。她没骂,没罚,只是指着沈青萝手帕上的寒梅:“沈家的梅花,当年开得比御花园的都艳。”那一刻,沈青萝忽然明白,太后什么都知道,只是不愿,或者说不能,再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偏殿的烛火灭了,龙床的帐幔还垂着。张昌宗跪在地上,听着武则天沉重的呼吸声,像听着自己命运的倒计时。他曾以为握住了权力的把柄,最后才发现,自己不过是武则天晚年权力棋局里,一颗注定被舍弃的弃子——就像当年她舍弃薛怀义,舍弃沈南璆,舍弃那些曾让她短暂忘却孤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