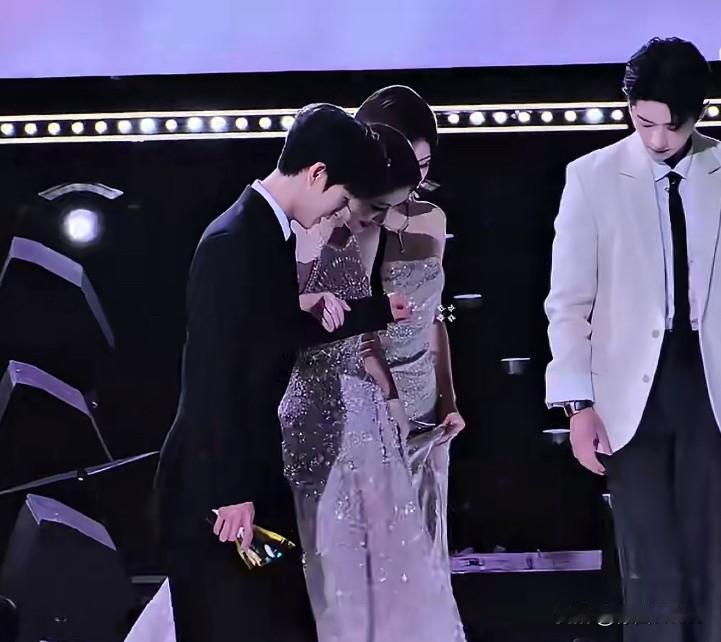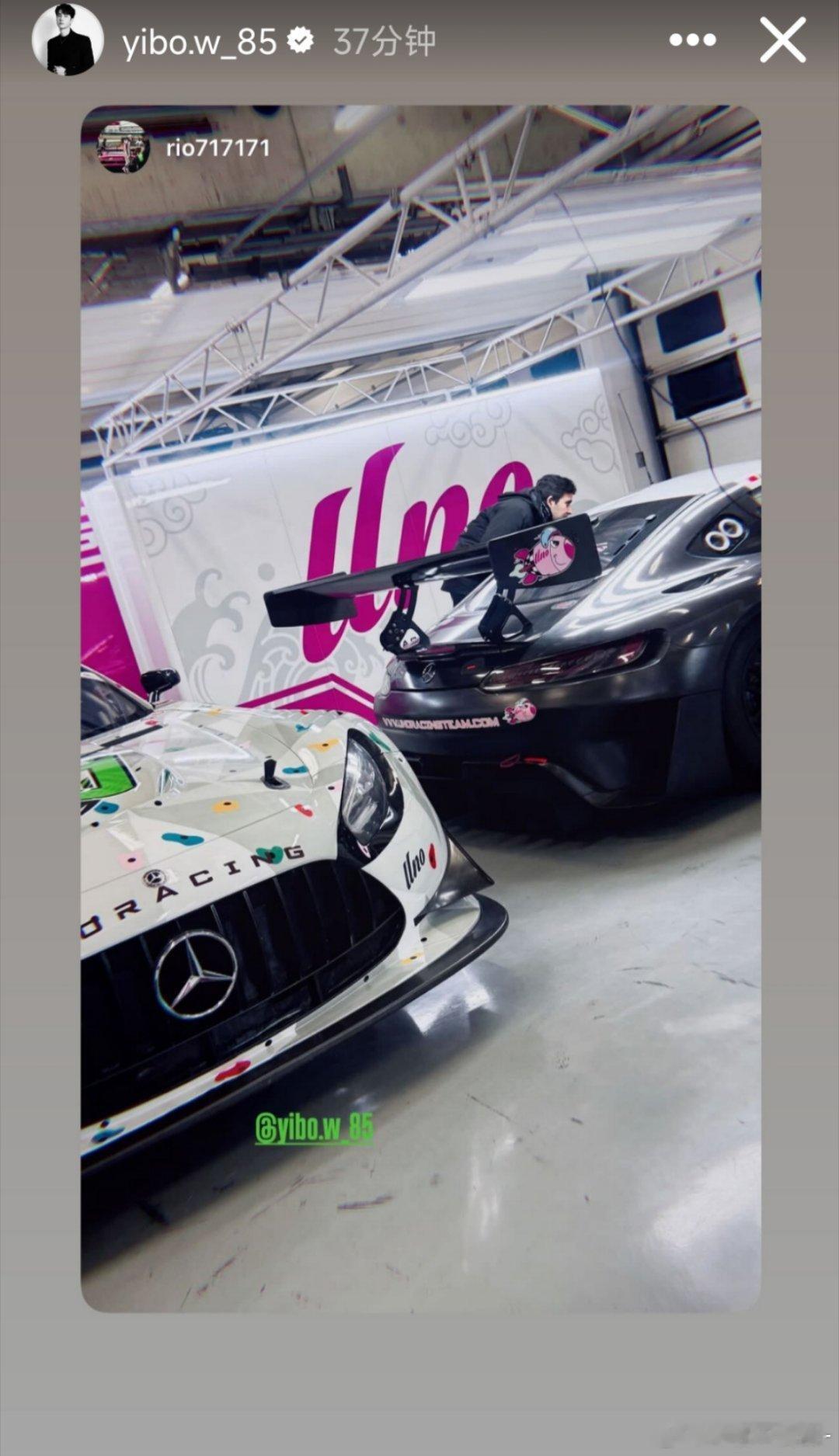小叔喝酒回家打了小婶两个耳光,小婶不哭不闹,做了晚饭,吃完倒头睡下,睡到半夜小叔感觉憋得难受,仿佛有大石压在胸口,迷糊间还没睁眼,一顿乱拳披头盖脸落了下来。“哎哟!谁啊!”小叔疼得嗷一声坐起来,头还晕乎乎的,开灯一看——小婶坐在床边,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满是红血丝,可就是没掉一滴泪。 结婚五年,小叔总爱喝几杯。 喝多了就管不住手,骂骂咧咧是常事,偶尔还会动两下。 小婶性子软,每次都低着头,等他酒醒了,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洗衣。 那天他推门进来时,酒气混着冬夜的冷风灌了满屋子,小婶正系着围裙在厨房切菜。 “啪!啪!”两个耳光落在脸上,声音脆得像摔碎了碗。 她没躲,也没哭,手还握着菜刀,菜板上的土豆丝切得整整齐齐。 然后继续切,下锅,盛饭,像什么都没发生。 小叔摔门进了卧室,她端着碗筷进来,放在床头柜上,自己坐在桌边吃完,收拾好,倒头就睡。 后半夜两点多,小叔睡得沉,胸口突然闷得发慌,像被人用棉被捂住了口鼻。 还没来得及睁眼,拳头就带着风砸下来,“哎哟!”他疼得蜷起身子,酒意醒了大半,“谁啊?深更半夜的!” 他摸黑去开灯,暖黄的光洒下来——小婶坐在床边,头发乱得像团草,睡衣皱巴巴的,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可那眼眶干得像晒裂的土地,一滴泪都没掉。 小叔愣住了,他以为她会哭,会闹,会回娘家,就像村里其他受气的媳妇那样。 可她没有,她只是盯着他,手还握成拳,指关节泛着白。 后来小叔才明白,她不是不疼,是疼到忘了哭;不是没气,是把气攒着,等一个没人看见的时刻,连本带利还回来。 他总以为她软,打了骂了,第二天做顿饭就过去了;却不知道沉默不是原谅,是堤坝,水满了,总会决堤。 那晚小叔抱着头蹲在地上,半天没敢抬头。 那扇紧闭的卧室门,好像从那晚起,就没真正敞亮过。 你看,人心不是棉花,揉皱了就再也展不平;有些伤,当时没喊疼,不代表后来不会让你疼得睡不着。 厨房的油烟味早就散了,可那股没哭出来的委屈,像根细针,扎在小叔后颈上,一转头就疼。
小叔喝酒回家打了小婶两个耳光,小婶不哭不闹,做了晚饭,吃完倒头睡下,睡到半夜小叔
凯语乐天派
2025-12-22 21:32:07
0
阅读: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