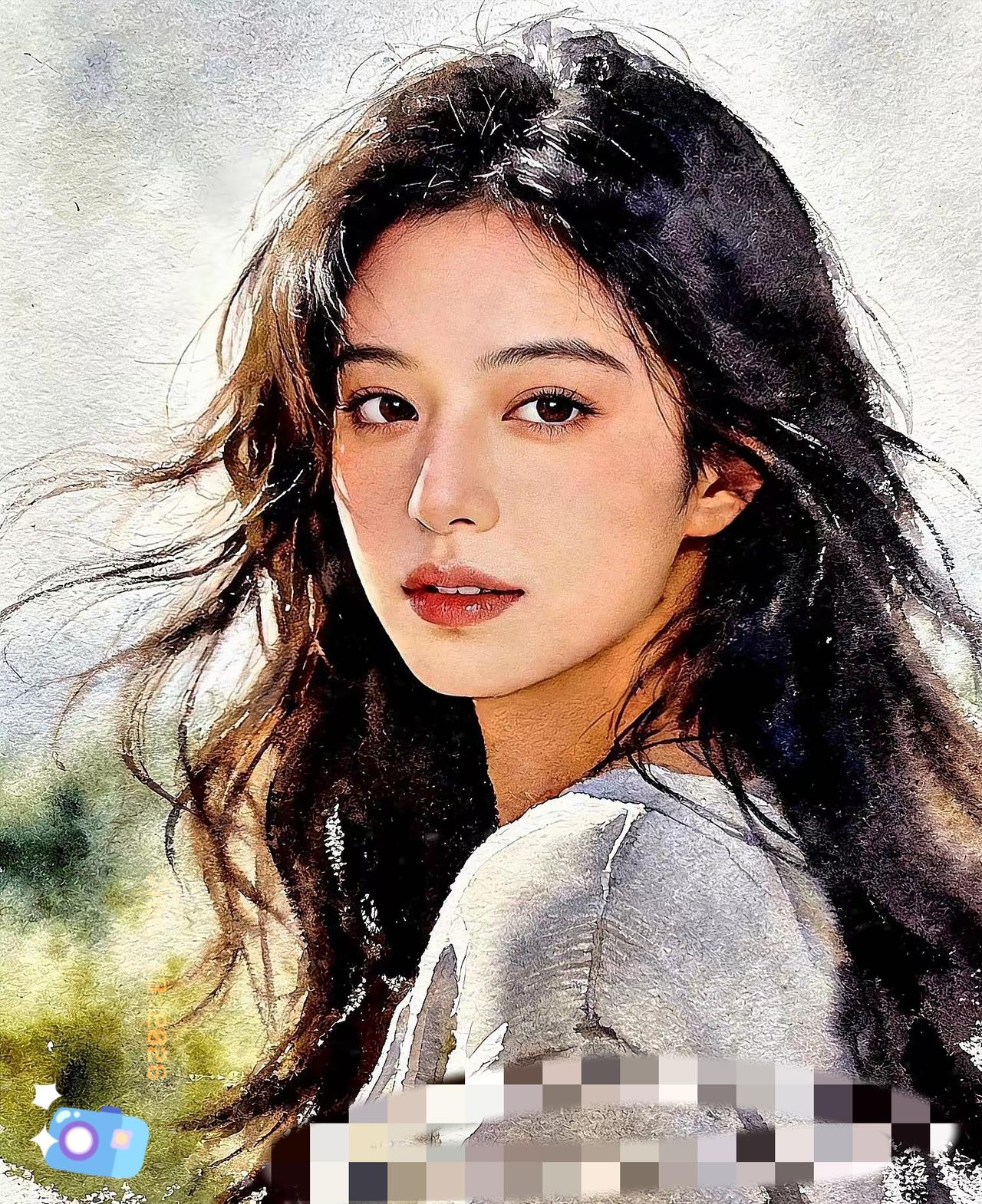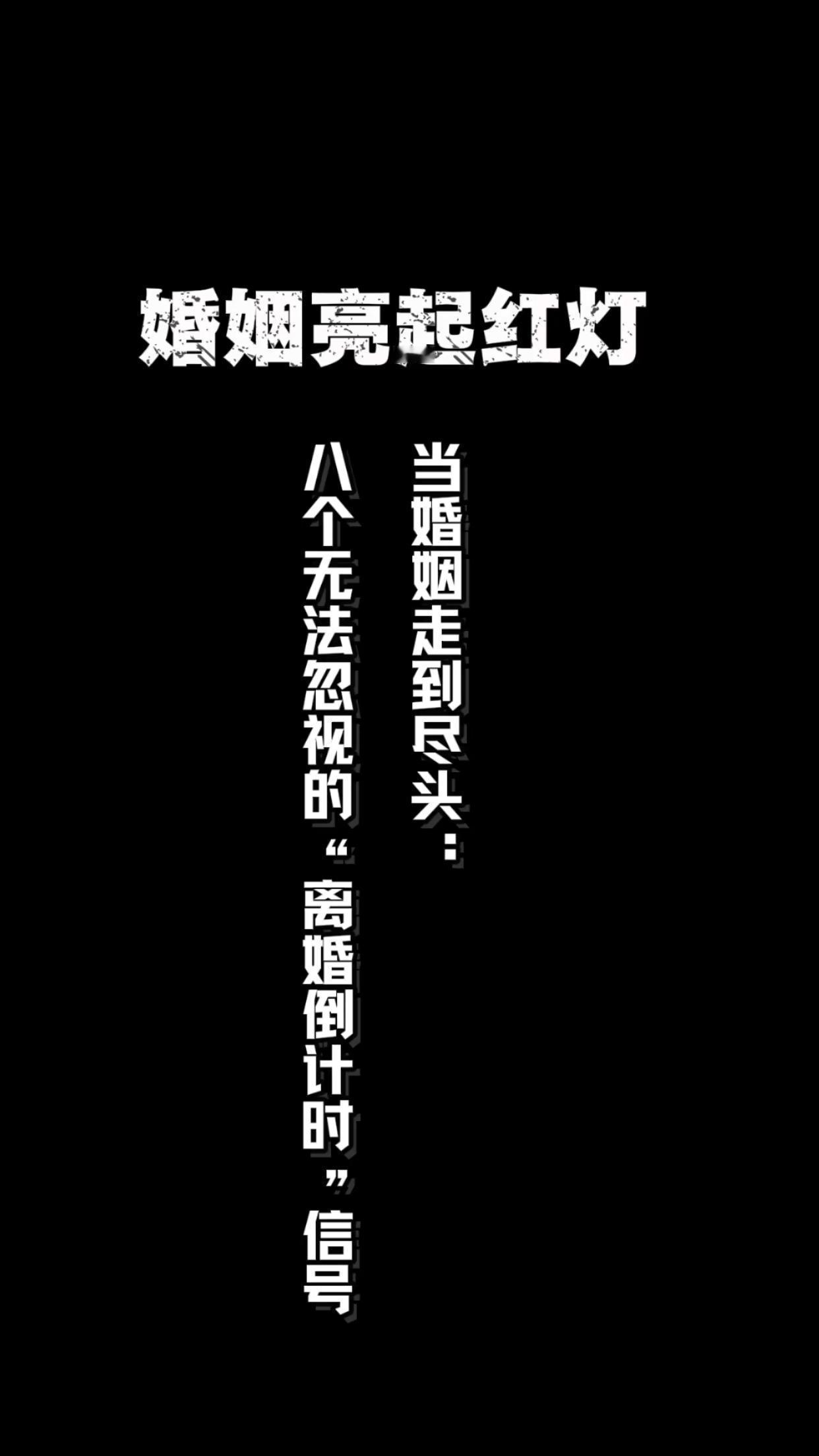1970年,女知青张菊芬热恋时,男友哀求说:“你就把身子给我吧,我会对你负责!”谁料,发生关系不久,男友就抛弃了张菊芬,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1969年前后,她随大批城市青年来到黑龙江讷河,在土炕上睡、在冻土里刨,窝头配咸菜成了家常。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同批男知青成了她生活里的火苗,在田埂上帮她分担活儿,在工棚里与她分着干粮。 日子再苦,有人说一句“我会对你负责”,就足以让一个19岁的姑娘相信,自己并不是一个人扛着天寒地冻。 1970年,关系越走越近,男青年用那句耳熟能详的“你就把身子给我吧,我会娶你”的誓言,换来了她最彻底的信任。可现实转身就给了她一记重击。 回城指标落到男方头上,他匆匆打点行李,有的只留下五元钱,有的连一句告别都没有,独自登上返回城市的列车,把张菊芬和她肚子里新生命,扔在了北大荒的风雪里。 怀孕的异常很快显现出来。在那个把“作风问题”看得比命还重的年代,未婚先孕不仅意味着羞耻,还可能被扣上“破坏知青政策”的帽子,轻则取消返城资格,重则处分乃至判刑。 流言像野草一样疯长,昔日姐妹渐渐疏远,干部严厉谈话,她一度绝望到想用土办法结束这一切,却在感到胎动时又下不去手。 幸好,连队里还有老支书、热心大娘这样的好人,把她悄悄安置在一间破旧的土坯房,用自家有限的口粮帮她熬过最难的几个月。 1971年一个飘雪的夜里,或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给孩子取名张淑凤,寄望这个在苦寒中降生的孩子,将来能像凤凰一样飞出这片黑土地。 然而,一个未婚女知青在那样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堂堂正正地抚养孩子。无论是档案、返城资格、还是今后的人生,都会被这个“私生子”撕得粉碎。张菊芬在无数个彻夜难眠的晚上反复权衡,最终咬牙做出决定,把女儿托付给当地一对无儿无女的农户。 交接的那天,她用唯一一件花棉袄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有人记得她还在襁褓上写下孩子的名字。木门关上的瞬间,她感觉心被硬生生劈成两半。从此,北大荒多了一个“上海知青的孩子”,上海则多了一个再不敢提起往事的女人。 70年代中后期,知青返城政策逐渐松动,大规模返城的浪潮终于席卷而来。张菊芬也跟着队伍回到了上海,有的说她终生未婚,把全部精力都倾在工作上,直到因病去世;有的回忆她后来结婚生子,成了一位普通的上海阿姨,每天骑车上下班,逢年过节陪丈夫和儿子逛街。 无论哪一种版本,可以确定的是,她把北大荒的那个女儿,牢牢锁在心底最深处,连最亲近的家人也鲜少提及。 而远在黑龙江的张淑凤,则在养父母粗糙却真诚的爱里长大。“上海知青的孩子”这几个字既是她的标签,也是她心中解不开的结。 她依稀记得3岁时,有一位女人轻轻摸她的脸,身上有淡淡的肥皂香,还有那件花棉袄的温度,这些零碎记忆后来成了她寻亲的全部线索。 成年后,她一边过着平凡的日子,一边被“我从哪里来”的疑问追着跑。她不怨母亲当年的抛下,只想搞清自己的身世。几十年间,她跑过无数当年的知青点,打听过上百位老知青,屡屡碰壁。直到2010年前后,她借助寻亲节目和媒体的力量,总算把线索一点点缩小到上海某个家庭。 当她第二次踏上上海的土地时,拎着那件珍藏多年的花棉袄,心里想着无数次想象过的重逢场景。可当门开的一瞬间,迎接她的不是白发苍苍、泪流满面的母亲,而是一个中年男人。 对方含泪告诉她,自己是她的舅舅,张菊芬早在几年前因病去世,有的说是2004年,有的说是2005年,无一例外的是,都提到她晚年时常失眠,多次在梦中惊醒。 舅舅承认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往事,却拒绝认亲,也不肯透露姐姐的墓地。他说,这是家族的耻辱,是不能被公开的秘密,姐姐的丈夫和合法子女都不知道这件事,不能因为一个突然出现的“北大荒女儿”,打破他们多年安稳的生活。 就这样,张淑凤带着那件花棉袄,在上海街头徘徊了几天,终究没能等来一句“女儿”。她唯一的心愿,不过是在母亲坟前磕个头,说一句“我不怪你”,却也被现实挡在门外。 这一段跨越四十多年的寻亲路,终于以无解收场。张菊芬用一生守住秘密,在沉默里消化自己的愧疚与恐惧;张淑凤用一生追问答案,在奔波中为自己寻找归属。她们一个把记忆封存,一个把记忆挖掘,最终都输给了时代留在她们身上的伤痕。 很多年后,人们再提起这段故事,不再只是指责谁薄情或谁软弱,而是看到那个年代里,个体在大潮中的渺小与无奈。有些母女,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拥有拥抱,却在彼此不知道的地方,为对方流了一辈子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