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和伟:“我初三复读的时候,班主任吴宏斌老师和我说:‘于和伟,你的成绩考高中费劲,而且你考上高中又能怎么着?你家庭条件又不好,你还要接着念大学吗?今年抚顺幼儿师范第一年招男生,分数线比较低,你可以去考这个学校,一毕业就有工作。 ’八十年代的抚顺冬天,零下二十度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 于和伟缩在母亲的烤地瓜炉旁边,看着炉子里窜出的火苗,心里头比这天气还冷。 三岁没了爹,母亲四十多岁才生下他,上面还有八个哥姐,一家人挤在漏风的平房里,唯一的棉被补丁摞着补丁。 本来想跟着哥哥去煤矿当学徒,至少能挣口饭吃,但母亲死活不同意,说砸锅卖铁也要让他读书。 复读班的日子更难熬。 同学带的白面馒头冒着热气,他揣的玉米面窝头硬得硌牙。 有次上课饿得头晕眼花,直接从椅子上摔了下去,全班哄笑的时候,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时候他自己都觉得读书没啥用,家里连几块钱的补课费都凑不齐,母亲夜里数毛票的声音,比任何道理都让人清醒。 吴宏斌老师就是这时候走进他生活的。 这位每个月挣58块工资的班主任,愣是从自己口袋里扣了8块钱给他交补课费。 本来想推辞,但吴老师塞给他一支永生牌铱金笔,笔杆上刻着“字如其人”,说这是借他的,以后出息了再还。 那支笔现在还在于和伟的书房里,笔帽都磨掉了漆。 吴老师不光管学习,还替他盘算出路。 1985年抚顺幼儿师范第一次招男生,毕业就能分配工作,这在当时可是铁饭碗。 于和伟一开始没看上幼师,觉得那是女孩子干的活儿。 但吴老师翻出辽宁省教育厅的文件给他看,说这里面有音乐、形体课,说不定你小子有这方面天赋。 就这么着,他半信半疑报了名,没想到真考上了。 幼师校园成了他的意外宝藏。 课程表上排着视唱练耳、儿童剧编排,这些本来觉得没用的东西,反倒让他找到了感觉。 校庆汇演他反串《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开口就把台下老师惊着了。 音乐老师拉着他说,你这嗓子不去唱戏可惜了。 那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只能去煤矿挖煤。 1989年抚顺话剧团招人,两百多个人争一个名额。 于和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把在幼师学的那套全用上,从擦皮鞋的侍者演到有几句台词的小角色,愣是留了下来。 跑龙套的三年里,他演了三十多个群众角色,每个角色的台词都抄在笔记本上,现在那本子还能翻出毛边。 后来想考上海戏剧学院,三百块钱的报考费难住了他。 姐姐知道了,啥也没说就把结婚时买的星海牌钢琴卖了。 拿到钱的那天,于和伟在琴房外站了很久,搞不清是该哭还是该笑。 进了上戏,同班同学有李冰冰、任泉,他是年纪最大的,也是最拼命的,每天最早到排练厅,最晚离开。 2021年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于和伟拿到最佳男主角,对着镜头说“没有吴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台下坐着头发花白的吴宏斌,两个人隔着人群对视,眼眶都红了。 这场迟到三十多年的道谢,比任何奖杯都让人心里发热。 如此看来,教育这东西有时候真挺奇妙。 它不一定非得是多宏大的工程,可能就是一位老师扣下的几块钱工资,一支旧钢笔,一句“你能行”。 于和伟的故事里,最打动人的不是他成了明星,而是那个在寒风里啃窝头的少年,真的被一束光拽了出来。 现在总说阶层固化,可于和伟和吴老师的故事告诉我们,总有人愿意为陌生人搭把手。 就像吴老师当年给他作文写的评语,“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每个普通人心里都有朵苔花,只要有人肯帮着浇点水,晒点太阳,说不定就能开得比牡丹还艳。 这大概就是教育最该有的样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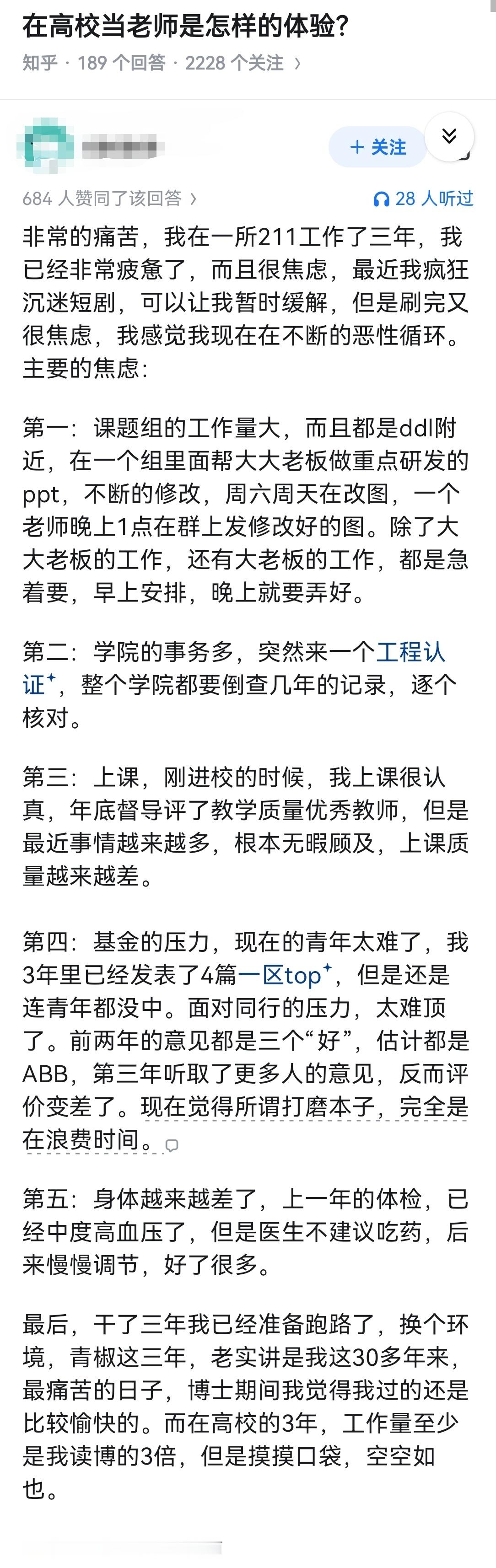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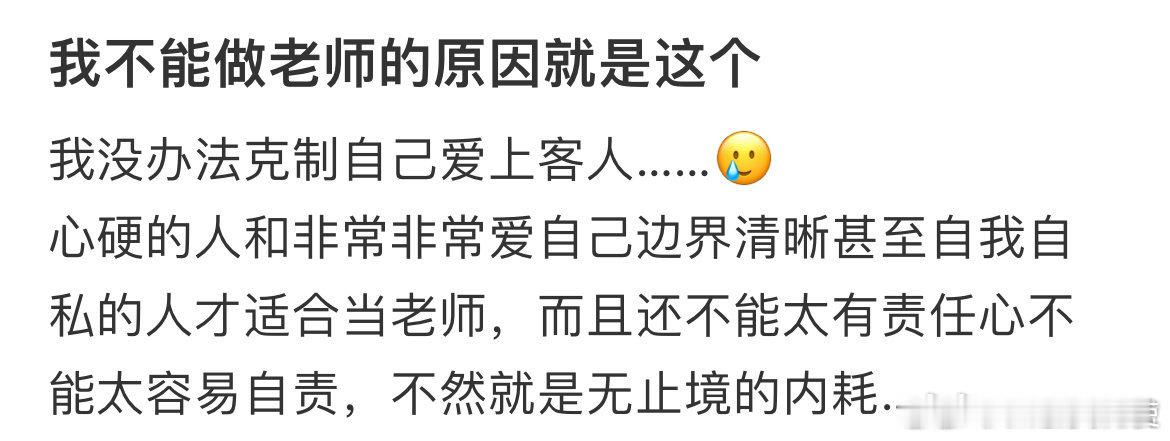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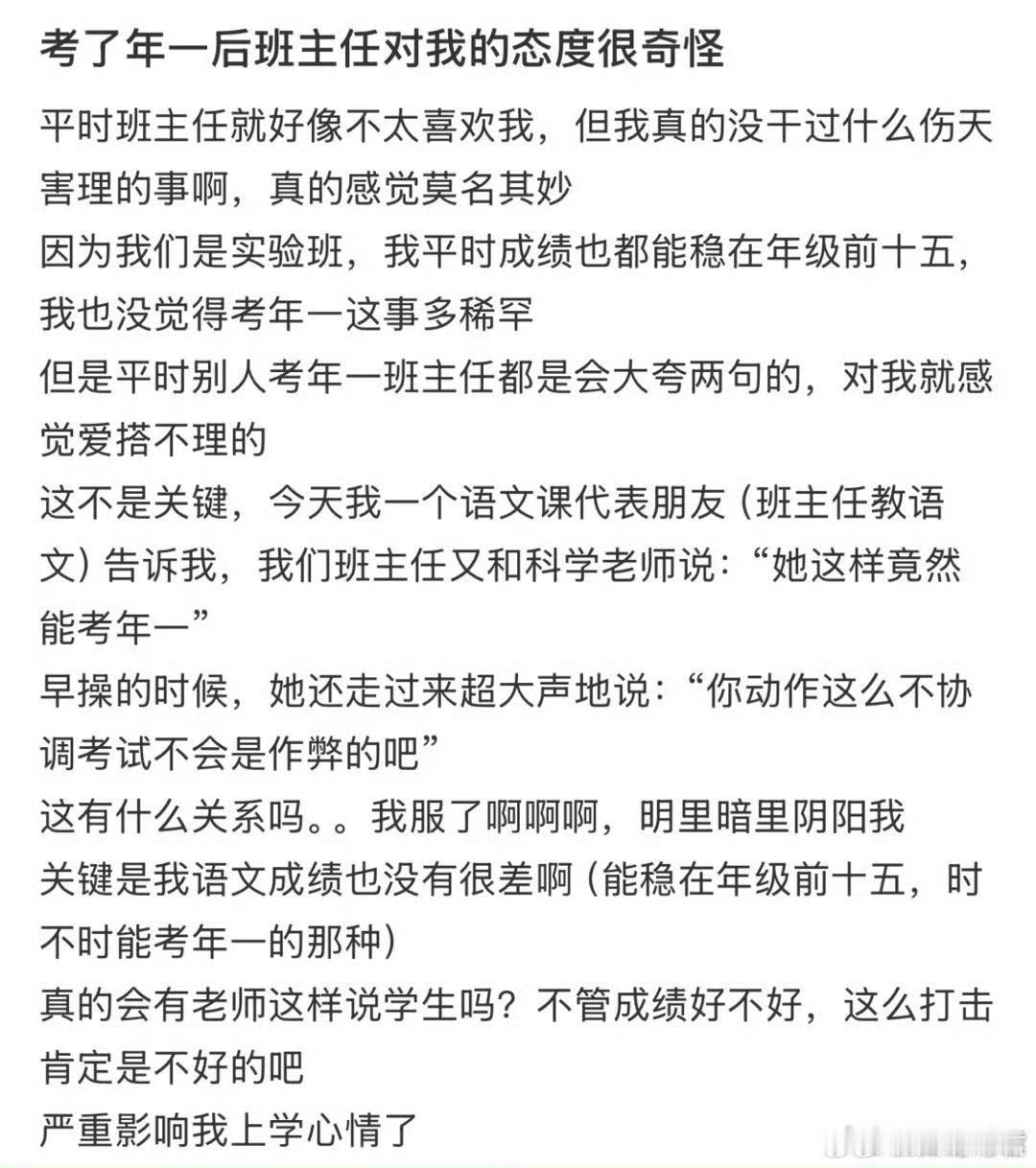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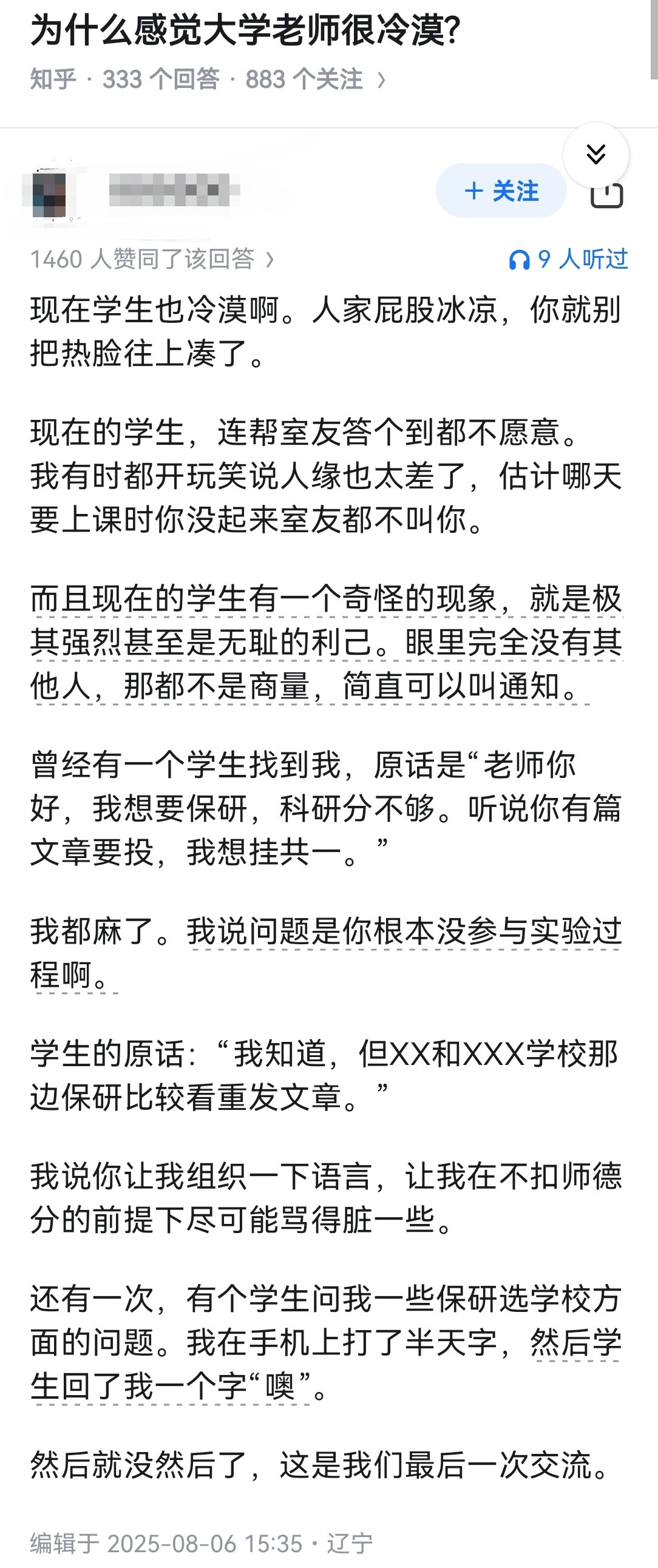



一念
遇到贵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