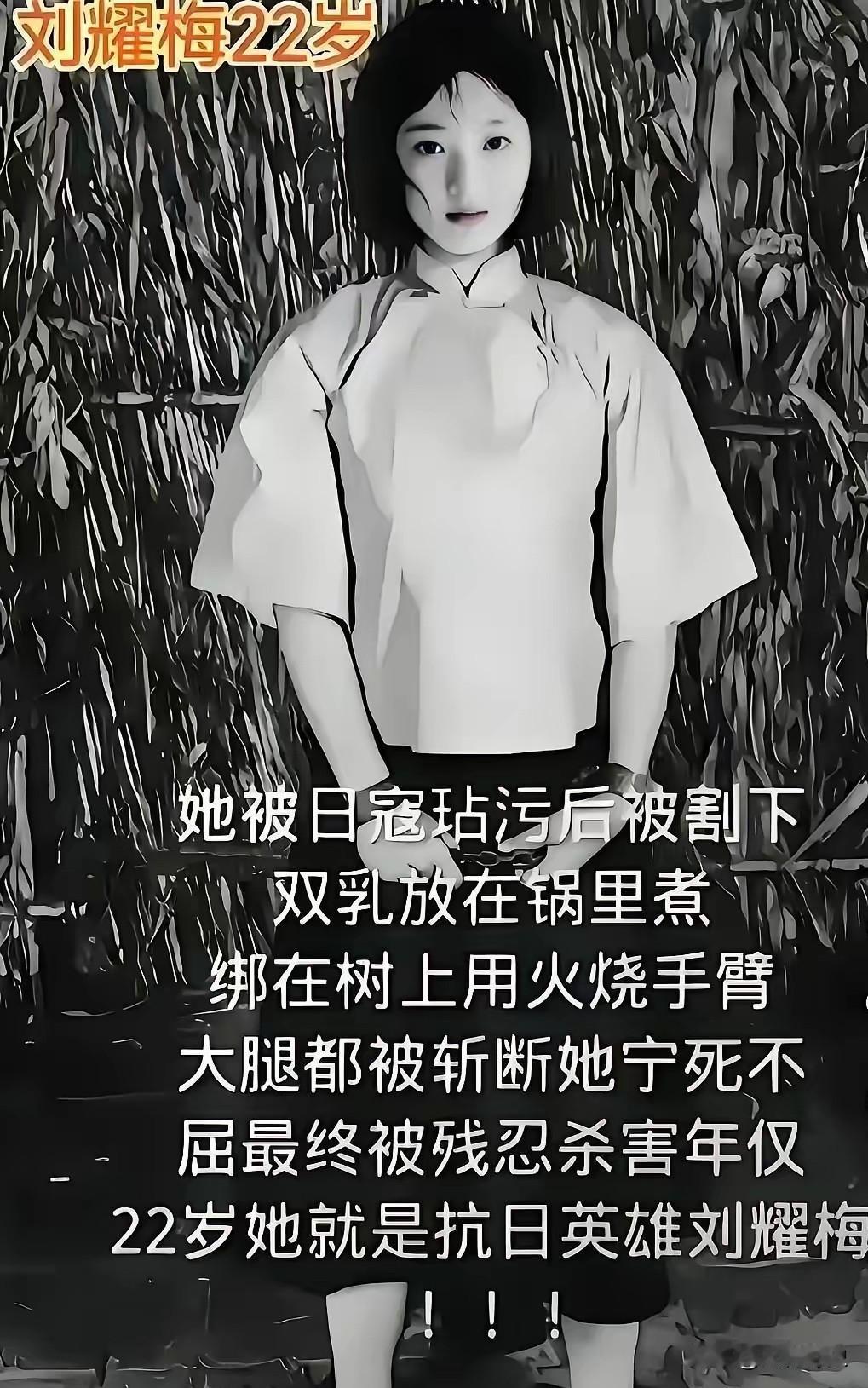1945年,在山上休息的迫击炮手陈宝柳,忽然发现30多个日军和几个女人,正在不远处的榕树下。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就悄悄架起迫击炮。打算给他来一发。 手指死死扣住冰冷的弹体,金属的凉意顺着指缝钻进来,像极了那年妹妹被抓走时,他握不住的那把锄头——同样的无力感,此刻却要变成救人的力量。 六十公斤的铁管压在背上,两年了,从浙江温州瓯海的田埂到华南山区的密林,这重量早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1922年出生的农家子弟,骨架大身板硬,种地是好手,被抓壮丁时却成了累赘。 谁能想到,这个曾在死人堆里装死的大个子,此刻正让炮弹长了眼睛?21岁那年第一仗,他吓懵了装死,爬回营地挨了团长一拳:“光长个子白吃饭!” 扔进大刀队“雪耻”,他拿着大刀嗷嗷冲,却被日本兵扎穿大腿。两次丢人后,两门迫击炮发到连队,别人被弹道计算搞得头晕,他摸着炮身就开了窍——不是聪明,是憋着一股火没处撒。 两百米外,榕树浓荫里,鬼子的酒壶碰得叮当作响,女人的啜泣像针一样扎耳朵。七八米的距离,82炮的杀伤半径是圆的,他得让死亡只在鬼子堆里开花。 “咣”的一声闷响!炮座后坐撞得肩膀发麻,他却盯着秒表;三秒一发,这手速是在病床上数着血滴练的。第二发、第三发接连入膛,死亡要像暴雨一样倾泻,不等敌人反应。 榕树底下炸开了锅,破片专找鬼子密集处飞,女人趁机往深山跑。他没数炸死多少,背起发烫的炮管就钻林子——打了就跑,这是他琢磨出的“步兵诱敌、重炮覆盖”战术里最实在的一条。 后来别人说这是“教科书般的炮击”,他只记得炮身那层温润的包浆,像岁月给他的勋章。 2015年,93岁的他胸前挂上抗战胜利纪念章,粗糙的手摩挲着章面,像当年摩挲那门炮。 从被抓壮丁到神炮手,再到田垄里的老农,他把传奇藏进泥土,就像那天消失在丛林里的炮声,悄无声息,却震耳欲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