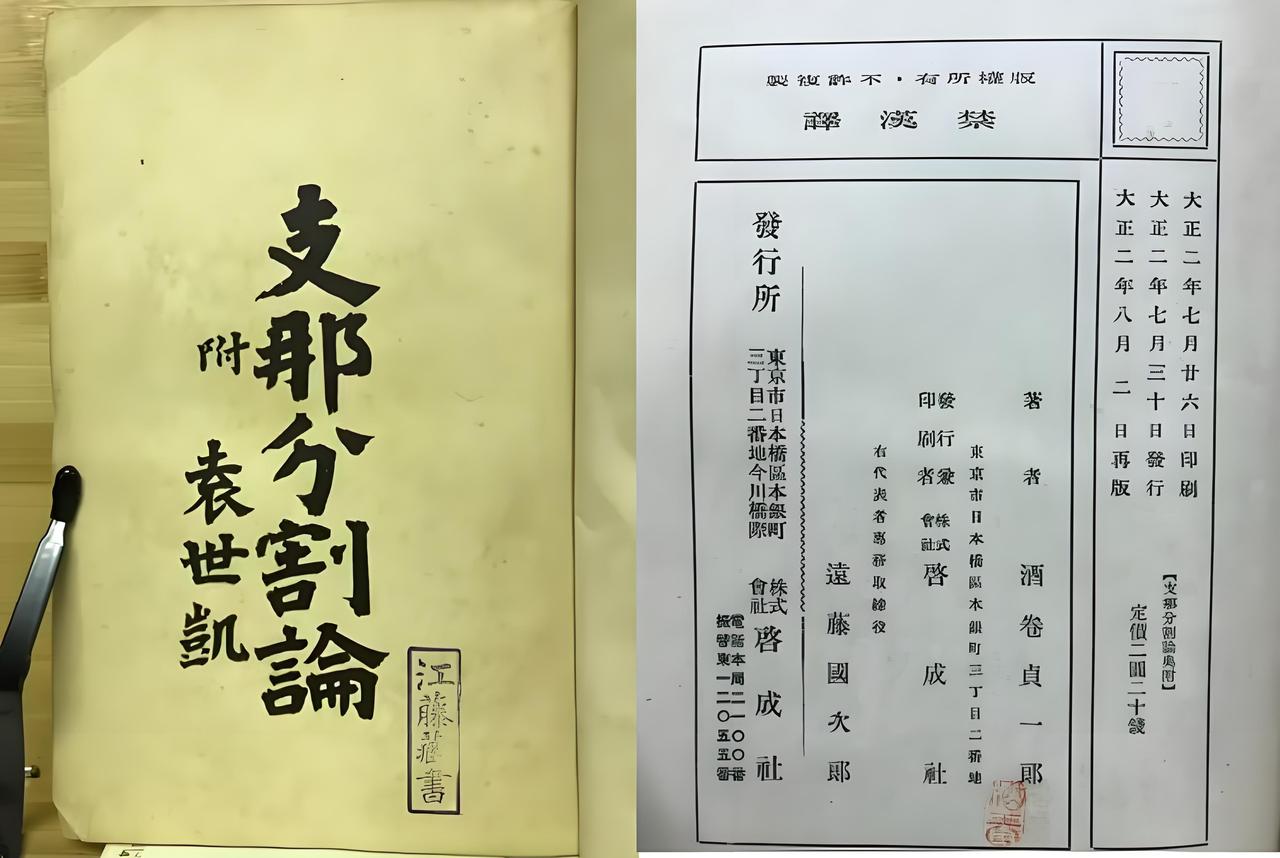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在房间挂了一幅日本女子的裸体画,妻子俞氏每次看见都忍不住恶心。 那幅画就挂在书桌对面墙上,油彩还泛着未干的光泽,俞氏端着茶水进来时,总要别过脸才能把杯子放在桌上。 俞氏比李叔同大两岁,是家里早在他十八岁时就定下的亲事。 那时候像她这样的女性,在京津一带士绅家庭里,一百个里也难有五个能自己选丈夫。 她嫁过来后就没见过丈夫对哪件事这么执着,他在日本学画那几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守着天津的老宅,把账本理得清清楚楚,连下人买菜的铜板都记在红皮册子里。 从日本回来的李叔同像换了个人。 他教学生画人体模特,把西洋乐谱带回课堂,连吃饭都要用银质刀叉。 俞氏不懂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有什么好看,更不明白丈夫为什么非要把光着身子的女人挂在墙上。 有次她趁丈夫外出,偷偷用蓝布把画遮了起来,结果当晚就被他扯了下来,两人在书房里沉默地对峙到后半夜。 1905年母亲去世后,李叔同突然把家里的事都交给俞氏,一个人提着皮箱去了东京。 后来俞氏才从丈夫朋友那里听说,他在日本有个叫雪子的女模特,两人一起演话剧,还合过一张穿和服的照片。 那些年俞氏守着空房,把三个孩子拉扯大,长子早夭时她都没敢告诉远在海外的丈夫。 三十八岁那年冬天,李叔同突然从杭州寄回一封信,说要在虎跑寺出家。 俞氏带着儿子赶到杭州,隔着寺院的木栅栏,看见曾经穿西装的丈夫穿着灰色僧袍,头发已经剃得锃亮。 她问他为什么,他只说“世间事皆有定数”。 那时候俞氏突然想起多年前被扯掉的蓝布,原来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捂不住。 弘一法师圆寂前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 他的弟子说,法师晚年常对着一幅旧画流泪,画里是穿和服的女子坐在樱花树下。 而天津老宅的红皮账本,最后一页停留在1918年,上面记着“买蓝布三尺,银一钱二分”。 俞氏没等到丈夫还俗就病逝了,临终前让人把账本和那幅被藏起来的裸体画一起收进樟木箱。 那幅让俞氏恶心了半辈子的画,后来在美术馆展出时,旁边的说明牌写着“中国近代人体艺术先驱之作”。 而弘一法师的僧袍,至今还保存在泉州开元寺,衣料磨出的毛边里,似乎还能看见当年用银刀叉划出的细微纹路。 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印记,最终都成了时光里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