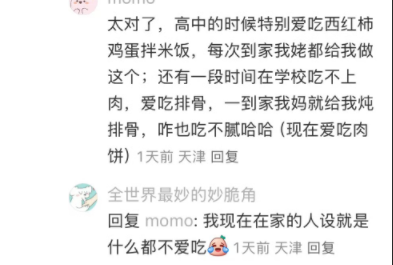我真的不理解我婆婆。公婆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有一万多,可他们的晚餐总是很简单:炖个鸡蛋糕、炒两个素菜,喝点小米粥,再蒸点馒头。反正就是怎么方便、怎么少油就怎么做。 傍晚六点半,厨房的日光灯管嗡嗡响着,婆婆正站在灶台前搅鸡蛋液,筷子碰到搪瓷碗沿,发出细碎的叮当声。 公婆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有一万多,可餐桌上永远是老三样:嫩豆腐似的鸡蛋糕,清炒的白菜或萝卜,一碗熬得稠稠的小米粥,还有几个圆鼓鼓的白面馒头。 我真的不理解。上周三我忍不住开口:“妈,明天咱们炖个排骨吧?我看超市肋排挺新鲜的。” 婆婆手里的锅铲顿了顿,没回头:“冰箱里还有半颗白菜,炒了吧,排骨贵。” 我撇撇嘴,心里嘀咕:一万多的退休金,还在乎这点排骨钱? 周末整理老相册,翻到婆婆三十年前的照片:穿蓝色工装,站在工厂食堂门口,手里端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缸沿还有个豁口。 “那时候工资三十七块五,养活你爸和两个孩子,一顿饭恨不得掰成三顿吃。鸡蛋都是过年才敢买的稀罕物,哪像现在,鸡蛋糕想蒸就蒸。”婆婆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指着照片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 我以前总问自己:明明有钱,为什么非要过得这么“委屈”? 现在好像有点懂了。她怕的不是没钱,是再回到那个连鸡蛋都要算计着吃的年代——那些日子教会她,简单不是苦,是经历过匮乏后,才懂的甜。 她蒸馒头时总多揉两遍面,说“面揉到位了才筋道”;炒素菜时油放得少,说“清淡了舒服”;小米粥熬得稠,说“稠点顶饿”。这些话背后,都是她和日子较劲的痕迹——不是不会享受,是那些苦日子让她觉得,踏实比什么都重要。 昨天我买了袋新米,她摸着米袋说“现在的米真白”,淘米时却把水接在盆里,留着冲厕所。我没像以前那样说“妈,这点水费不值钱”,只是帮她把米倒进锅里。 傍晚的厨房还是老样子,日光灯管嗡嗡响,婆婆搅鸡蛋液的手稳得很,筷子碰着搪瓷碗,叮当,叮当。 蒸好的鸡蛋糕端上桌,我舀了一勺,嫩得像云朵。 原来,她不是不理解现在的好日子,是她用自己的方式,把好日子过得更长久些。 而我,终于学会在这简单里,尝出点不一样的味道了。
刘卫东被留置那天,北方公司食堂的酱香排骨照样卖空,谁也没把这事和风光的刘
【102评论】【137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