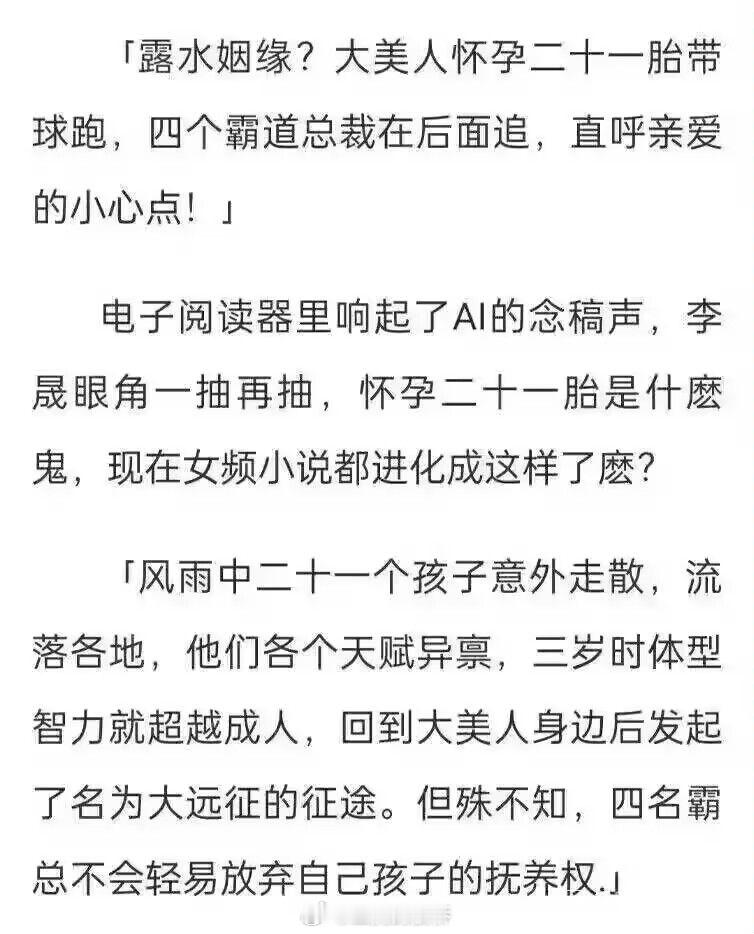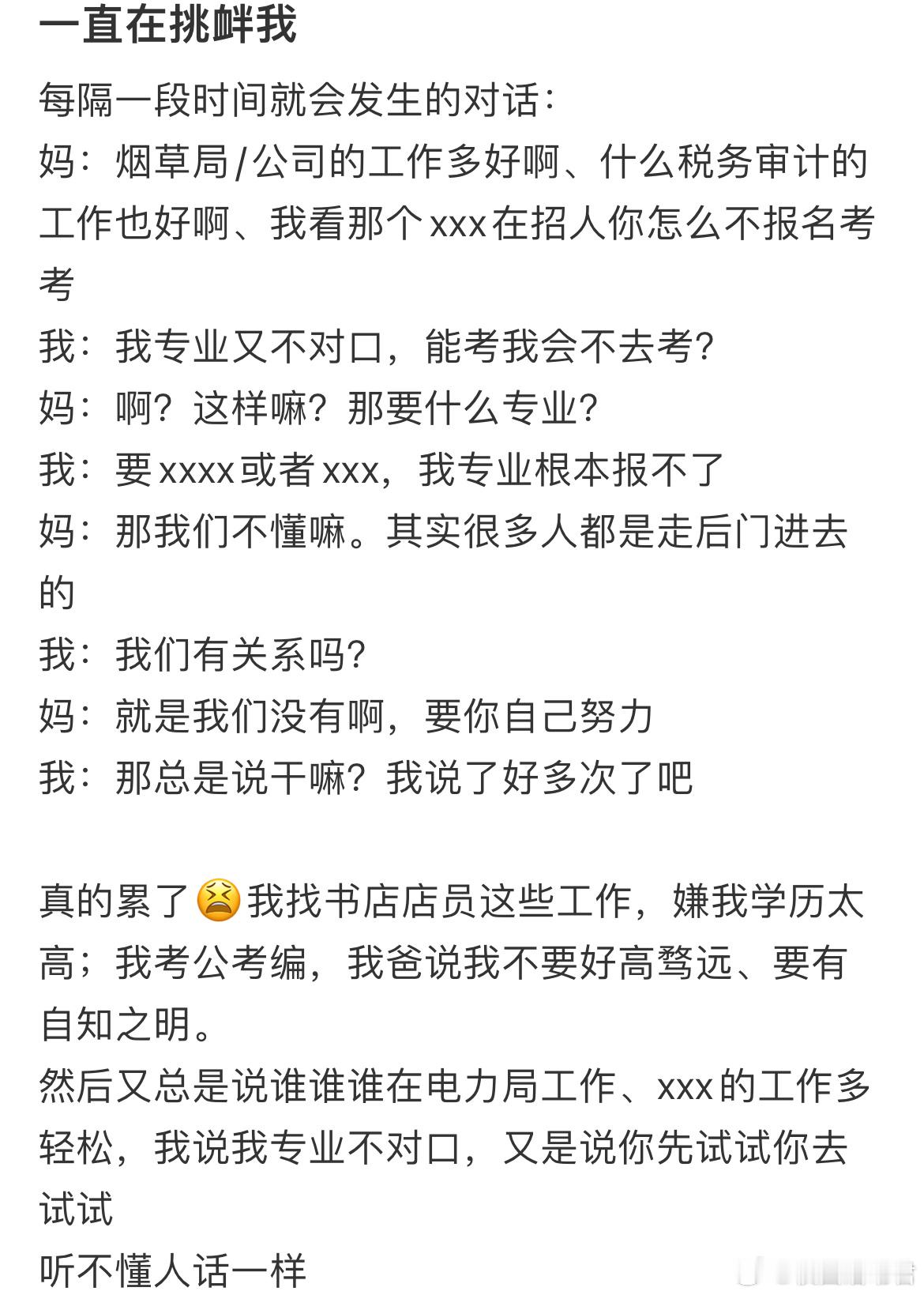一位社会学家非常犀利的话: “你孩子进不了好单位,不是孩子不行,而是你不行。你孩子找不到对象,30%是孩子不行,70%是你不行。你没有能力让孩子上好学校,你没有能力花大几万让孩子参加各种昂贵的夏令营提升认知开拓眼界,你没能力让孩子尽早买上婚房,买上好车,甚至因为拿不出彩礼钱,谈了几年的对象说散就散了。孩子终于挤过独木桥考进了体制内,因为没有人脉关系,照样在底层打杂,很难往上爬。现实中的你不行是真的即糟糕又扎心。” 老周把熨好的西装递给儿子时,手指在那截没剪的标签上摩挲了一下,三千八,他两个月退休金。 “爸,放心。”儿子声音发干。今天面试那家国企,五百人抢两个名额。 老周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想起三十年前自己考棉纺厂,母亲煮了三个鸡蛋塞他兜里。 那时以为努力就能轧出一条路,现在知道,路早被不同的车占着了。 晚上儿子回来,外套搭在肩上。妻子在厨房炒菜,油烟机轰隆隆响,盖过了沉默。老周看见儿子指甲缝里还有点面试表格的蓝印泥。 “笔试第二,”儿子扒着饭,“面试……问爸爸是做什么的。” 老周嚼着米饭,忽然尝出铁锈味。他是货车司机,开了一辈子长途,最远到过广州。这个身份在表格“家庭情况”栏里,只需填一行。 周末亲家来吃饭。准亲家母说起同事女儿嫁了医生,婚房在江边。 妻子端上的螃蟹,她只挑了一只最小的。“小峰工作定了吗?”她问得随意,像问菜咸不咸。 老周给儿子夹了只蟹钳。他想起年初,亲家暗示过彩礼数。 儿子那时说:“爸,我再攒攒。”可怎么攒?儿子在培训机构代课,课时费像雨季的水滴,时有时无。 深夜,老周在阳台抽烟。楼下停着那辆老货车,明天还得去拉建材。 妻子过来,递给他一件毛衣:“肩膀又疼了?”他点头,妻子便站身后给他揉。 她的手也糙了,揉的动作却还像三十年前一样轻。 “要不,”妻子声音很小心,“找我表弟借点?他在开发区……” “不借。”老周打断得很快。去年表弟家孩子结婚,他包了五千。人家回礼是一条烟。 他知道,那是清账的意思。 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老周想起父亲临终时的话:“我这辈子,没给你们兄弟仨留下什么。” 那时他年轻,觉得父亲糊涂。现在懂了,父亲说的是真的。 有些东西,不是靠力气就能挣来的,像人脉,像关系,像那些酒桌上拍拍肩膀就能办成事的交情。 儿子房间还亮着灯。老周掐灭烟,轻轻推开门。儿子在看公务员考试题,台灯照出耳侧新生的白发。 “爸?”儿子抬头。 “早点睡。”老周只说这一句。他想摸摸儿子的头,像小时候那样,可手伸到半空,只拍了拍肩膀。 那西装挺括的料子,在手心里凉凉的。 就像他那颗早已千疮百孔,却又无可奈何的心。 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现实社会,普通家庭为了托举儿女,掏空积蓄付首付、咬牙借钱凑彩礼,试图用钱去填平那条起跑时就存在的鸿沟。 到头来,还是很难翻身逆袭。 道家《阴符经》讲:“日月有数,大小有定。” 其实,天地运转有其定数,社会资源分配也早有看不见的刻度。 普通父母拼尽全力托举的高度,或许只是某些家庭孩子出生的起点。 这不是认命,是认清:我们的战场,本就不在同一片平原。 佛家讲“共业”,一个家族的境遇,是时代、环境和认知交织而成的网。 父母之“不行”,往往是他们那代人的信息、机遇与局限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实,很多时候,最难打破的就是现实的壁垒。 所以,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不是成为巨人,而是成为一块稳当的垫脚石,并且告诉孩子。 看到远方了吗?那才是你要自己去走的路。 你埋怨父母的那个“你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