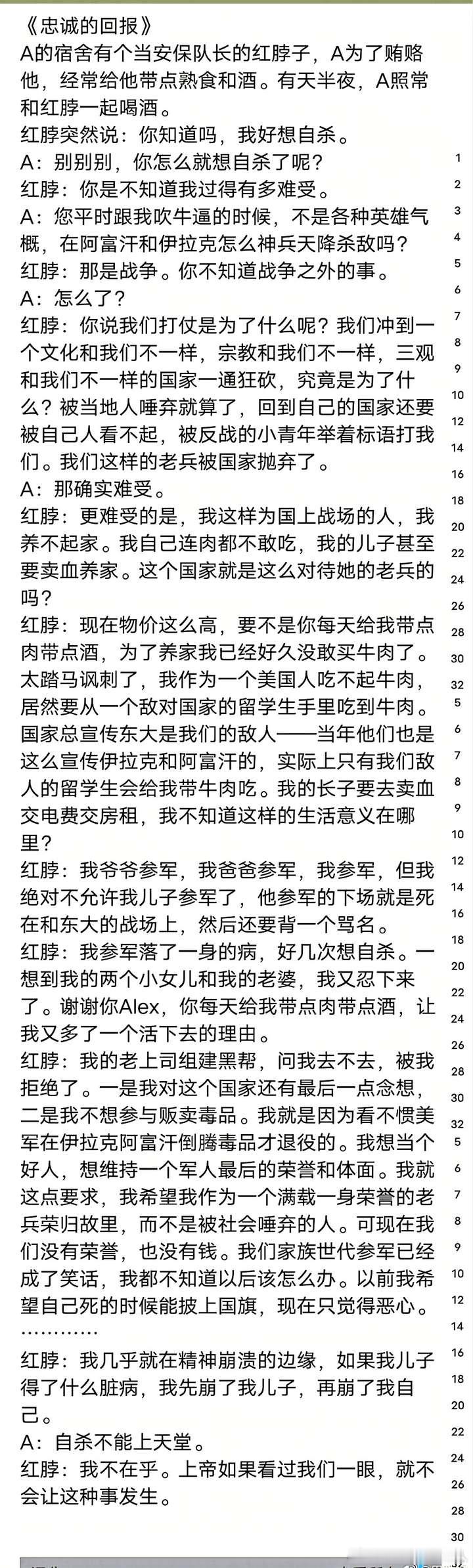抗日战争时,“打完鬼子吃顿饭,战友们都得了一种怪病,白天脚肿得很粗,头正常,晚上头肿得很大,脚却变得很细,口鼻出血......” 1937年深秋,四川农村的稻田还结着霜,18岁的我跟着队伍踏上了出川的路。 脚下的草鞋磨得脚底板生疼,身上背着的土造步枪比我还高。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亡国,只记得村长说“你们走了,家里的田我帮着种”,这句话让几百个四川娃子红了眼眶。 到了长兴地界,才知道战场比说书人讲的还可怕。 日军的坦克像铁壳子怪兽,我们手里的手榴弹扔过去只能听个响。 老兵教我们把炸药捆在身上滚到坦克底下,第一个这么做的是邻村的二娃,他刚娶了媳妇,口袋里还揣着红盖头的碎片。 那十三天里,漫山遍野都是“雄起”的喊声,后来才知道,这喊声里有八千多个四川汉子再也没能回家。 泗安镇的土墙上至今还留着弹孔,只是现在爬满了牵牛花。 那天我亲眼看见师长把遗书塞进怀表,他说“你们活着看到胜利,就把这个给我婆娘”。 后来听说他孤身冲向敌阵时,怀里还揣着半截没吃完的红薯,我们已经三天没正经吃过饭了,后勤队早被打散,能找到的只有地里冻硬的土豆。 怪病就是那时候开始出现的。 先是炊事班的老王,白天走路时裤腿绷得像灌了铅,到晚上脑袋就胀得像要裂开。 军医说可能是饿出来的,可我们哪有粮?后来才发现,这病专找最能打的汉子,他们总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员。 我亲眼看着一个能扛着机枪跑三里地的班长,第二天早上就硬在了战壕里,嘴角还挂着血丝。 撤退到南京城外时,我左腿中了一枪。 卫生员用刺刀剜子弹时,我听见远处传来“南京城破了”的哭喊。 迷迷糊糊中被抬上担架,最后看见的是弟兄们举着大刀冲向坦克,他们连手榴弹都用完了。 再醒来已是半年后,医院墙上贴着“抗战必胜”,可我知道,145师的番号,可能已经随着南京城里的硝烟散了。 去年我回了趟长兴,当年的战场现在盖起了纪念馆。 玻璃柜里摆着一双草鞋,跟我当年穿的一模一样,鞋底磨穿了三个洞。 讲解员说这是从烈士遗骸上找到的,我摸着玻璃突然想起,二娃当年总抱怨他的草鞋不如我的结实。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了块褪色的红布,是当年出川时娘塞给我的,说“见红就能平安”。 现在我把它压在师长遗书的复印件下,那上面“决以一死以报国家”八个字,比任何勋章都重。 这些年总有人问我川军凭什么打赢,我想说,我们赢的不是武器,是把最后一口粮让给兄弟的情分,是明知要死还往前冲的憨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