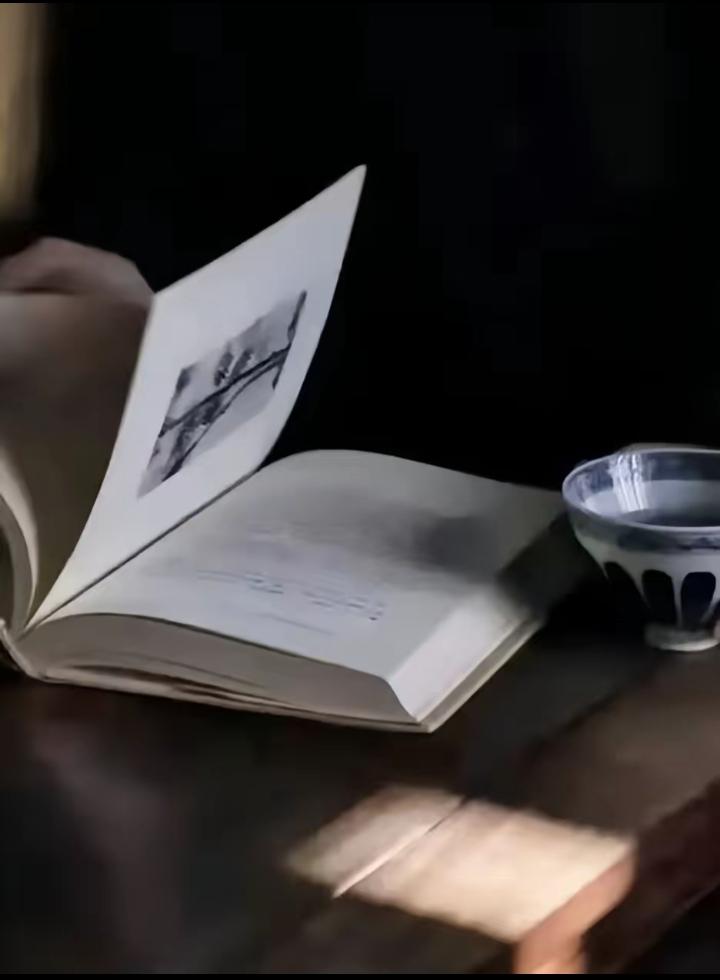我老家隔壁的邻居老周,大半辈子都在外地工地上讨生活,他三十五岁离婚那年,在南方的工地上,跟一个家里有丈夫的女人,做了半年的临时夫妻。这事是他过年喝多了,坐在我家门槛上,一句一句跟我唠出来的。
老周离婚那年,闺女刚上小学,跟着前妻在老家生活。他没什么别的本事,就会干工地的活,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了五六年,熬成了个带班的,手底下管着十几号工人,比普通小工赚得多点,也能在工地上说上几句话。
那年夏天,南方的雨下得邪乎,连着半个月的大暴雨,工地上的铁皮棚,十间有八间都漏雨。
老周跟我说,那天晚上的雨特别大,砸在铁皮棚顶上哐哐响,震得人耳朵发麻。他正蹲在地上,把铺盖往不漏雨的墙角挪,棚子的门帘突然被人掀开了。
门口站着个女人,叫陈秀,跟他一个工地的,先是在食堂帮过厨,后来也去工地上干杂活。她裤脚卷到膝盖,上面全是泥点子,手里攥着块皱巴巴的塑料布,头发湿哒哒地贴在脸上,嘴唇冻得发白。
她开口,声音哑得厉害,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恳求:“周哥,我那棚子漏得实在没法住人了,你这儿……能不能让我挤一晚上?”
老周在工地上待的年头久了,见多了工地上男女搭伙的事。都是背井离乡出来讨生活的人,家里有牵挂,身边没个伴,凑在一起互相搭把手,暖个身子,等工程结束了,就各回各家,各找各的人,彼此心照不宣。
他看着女人浑身湿透的样子,没多犹豫,点了点头,跟她说:“就一张铺,不嫌弃就进来。”
那女人没多说一句废话,进来就把手里的塑料布搭在棚顶漏雨的横梁上,又搬了两块砖头压牢,动作麻利得很。
铺位只有一米二宽,她挨着老周躺下,隔着两层洗得发白的工服,能清清楚楚感觉到彼此的体温,还有轻轻的呼吸声。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棚子里又闷又热,空气里混着她身上的皂角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汗味,是每个在工地上卖力气的人,身上都有的味道。
“周哥,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女人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哭腔。老周侧过头,借着棚子外面透进来的一点微光,看见她正抬手抹眼泪。
他抬起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跟她说:“慢慢熬,有我在,以后活我给你安排轻点的。”
女人突然就往他这边靠了过来,脑袋抵在他的胸口,胳膊环住了他的腰。老周没推她,反手就把她搂在了怀里。
老周跟我说,那天晚上,铺位太窄,翻个身都费劲,他们就那么挤在一起,汗混着从棚顶渗进来的雨水,把工服浸得透湿。女人咬着他的肩膀,不敢出声,只偶尔漏出一点细碎的哼唧。
他贴着女人的耳朵,跟她说:“以后,我护着你。”
女人嗯了一声,眼泪蹭在他的脖子上,烫得他心口发慌。
从那晚之后,他们就正式搭伙过了。
没说什么山盟海誓,也没定什么死板的规矩,就是两个苦命人,各取所需,互相搭把手。
女人每天收工回来,给老周洗衣做饭,把他那乱得像猪窝的铁皮棚,收拾得干干净净。早上老周上工前,总能喝上一碗热乎的粥,晚上回来,总有两个热乎的菜等着他。
老周也没亏待她。他是带班的,工地上重活累活多,他总能给她安排些轻松的杂活,不用顶着大太阳爬高上低。他知道女人的男人在老家摔断了腿,干不了重活,家里两个上学的娃,还有卧病的婆婆,全靠她一个人挣钱撑着。手里宽裕的时候,他总会偷偷塞给她点钱,让她别太委屈自己,也帮她垫了不少还债的钱。
工地上的人都看在眼里,明面上没人说什么,背地里难免嚼舌根。他们都当没听见,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能有个人互相暖着,比什么都强。
他们默契地从来不提家里的人,也从来不谈以后。
老周跟我说,他们都清楚,这样的关系,见不得光,也走不远。就像工地上的铁皮棚,只是临时落脚的地方,不是真正的家。
可那些难熬的日夜里,他们给彼此的那点温暖,却是实打实的,掺不了一点假。
转眼就到了年底,工地要停工了,大家都收拾着东西,准备回老家过年。
他们也在收拾棚子里的东西,女人把老周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背包里,还把自己腌了大半年的萝卜条,装了满满一罐子,硬塞到他包里,说他回去煮面条的时候能就着吃。
老周给女人准备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他攒了大半年的三万块钱,让她拿回去给男人做手术,给娃交学费。
女人推了半天,红着眼圈不肯要,跟他说:“周哥,这半年已经够麻烦你了,这钱我不能要。”
老周硬把信封塞到了她的行李包里,跟她说:“拿着吧,就当是我这个当哥的,帮衬你一把。回家好好过日子,以后要是有难处,还能给我打电话。”
腊月二十八,他们在火车站分开。女人坐往南的车,回她的老家,老周坐往北的车,回我们这个北方的小县城。
检票前,女人站在老周面前,看了他好半天,突然伸手抱了他一下,很快就松开了。
她跟老周说:“周哥,谢谢你。过年好。”
老周看着她红了的眼眶,喉咙发紧,半天只说出一句:“过年好,路上注意安全。”
女人转身进了检票口,没再回头。老周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手上好像还留着她身上那股熟悉的皂角味。
老周跟我说,过完年,他又换了个新的工地,再也没见过那个女人。
她从来没给他打过电话,他也没再主动联系过她。
他们都清楚,那年夏天暴雨夜里开始的那场搭伙日子,就像一场短暂的梦。梦醒了,他们都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扛起各自的责任,继续往前走。
现在老周已经五十多了,闺女早就大学毕业,在外地成了家,他还是一个人过,偶尔出去打打零工,大部分时间都在老家的院子里,种种菜,晒晒太阳。
每年过年,他都会拿出那个装过萝卜条的玻璃罐子,擦得干干净净,放在堂屋的柜子上。
他从来没跟村里其他人提过这事,也就喝多了的时候,会跟我这个隔壁的晚辈,唠上两句。
他总说,他们都是这世间讨生活的普通人,没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只有在熬不下去的苦日子里,互相给过的那一点,实实在在的温柔。
这辈子,能遇上那么个人,暖过那么一段日子,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