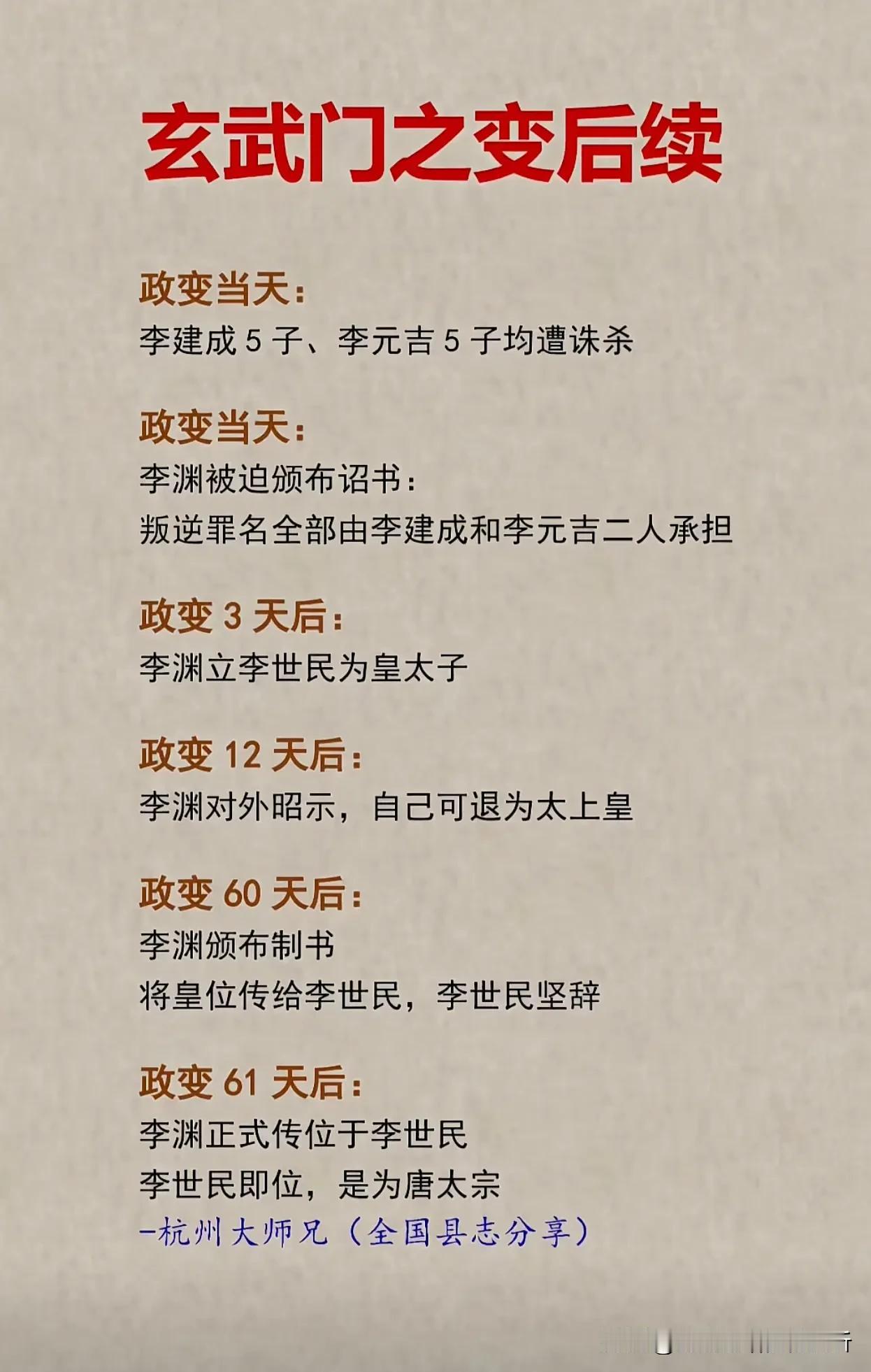1983年南方小城的夏日午后,露天审判台上的青年低着头,胸前木牌上"流氓犯"三个字被阳光晒得发白。 台下上万双眼睛盯着他,有人愤怒地扔出烂菜叶,他下意识缩了脖子,手铐在腕间勒出红痕。 公审大会开得很快,没有冗长的辩护。 法官念完判决书时,扩音器发出刺耳的电流声。 "死刑,立即执行"六个字像冰雹砸在人堆里,后排有人踮脚往前凑,想看清这个"玩弄女性"的男人长什么样。 他被押下去时回头望了一眼,人群里似乎有熟悉的身影,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那个年代的治安形势确实紧张。 街头巷尾总能听到谁家东西被偷了,哪个工厂的女工下班路上被骚扰了。 邓小平在那年夏天拍了板,要"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各地很快搭起这样的审判台。 只是没人想到,"流氓罪"这个筐,最后装了多少生活作风问题。 邻居王大妈至今记得那天举报的情景。 她扒着墙缝看见青年带不同女孩回家,煤油灯亮到后半夜。 在居委会开的治安会上,她拍着桌子说"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 当时街道干部拿着小本子记,第二天派出所就来人了。 谁也没问那些女孩是不是自愿,更没人考虑他们是不是在谈恋爱。 演员迟志强的案子差不多同时发生。 他在剧组和朋友跳贴面舞,被人举报后也定了流氓罪。 不过他运气好,只判了四年。 1997年修刑法时,学者们争论了很久。 有人拿出秦德宝案,那个因为同性恋被定流氓罪的小伙子,在监狱里关了五年才平反。 最后大家决定把这个"口袋罪"拆了,分成寻衅滋事、强制猥亵这些具体罪名。 法律条文里终于删掉了"其他流氓活动"这几个模糊的字,法官再也不能随便给人定罪了。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谈恋爱也可能犯法。 那个夏天在刑场上低头的青年,如果能活到今天,或许会在公园里看大爷下棋,或许正给孙子讲过去的事。 只是历史没有如果,他留在1983年的那道回望的眼神,后来成了法治课上反复提起的警示。 刑法课本里印着1997年修订前后的条文对比,泛黄的纸页上,"流氓罪"三个字被红笔圈出来。 老师说这是用很多人的代价换来的进步,法律终于学会了不随便干涉成年人的私人生活。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刚好落在"罪刑法定"那行字上,亮得有些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