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收废品的男人,他看我蹲在路边啃半块发霉的馒头,就把我领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本来是要去隔壁村收废铁的,走错路才遇见我。那天的夕阳特别红,照得他的三轮车像着了火。 我五岁那年,村里的路还是土路,一下雨就黏得能拔鞋。那天没下雨,日头毒得很,我蹲在大队部墙根啃馒头——馒头皮上的绿霉像撒了把碎草籽,咬一口,苦得舌头打卷。 他就是这时候来的。 三轮车“哐当哐当”停在我面前,车斗里堆着压扁的啤酒瓶和旧纸箱,一个铁架子歪歪扭扭支着块写“收废品”的木牌。男人跳下来,蓝布衫后背全湿透,印出脊梁骨的形状。他没问我家在哪,就蹲下来看我手里的馒头,问:“好吃不?” 我没说话,把馒头往身后藏。他忽然笑了,从车斗里摸出个油纸包,里头是块红糖发面饼,还热乎着。“给你,”他塞我手里,“这个比发霉的甜。” 我不敢接,他就自己拿起我那半块发霉的,掰了一小口,嚼得咯吱响。“嗯,有点苦,”他咂咂嘴,“但饿肚子更苦。” 那天他没去收废品,就坐在我旁边,看我小口啃饼。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三轮车的铁皮反着光,真像着了火。他说:“跟我走吧,以后有甜饼吃。” 我就跟他走了。 后来才知道,他本来要去隔壁村收废铁,前一晚轮胎被钉子扎了,绕路时迷了方向,才拐进我们村。邻居婶子说他傻,“收废品的还捡个拖油瓶,不是给自己找罪受?”他总是嘿嘿笑,晚上却会把碗里的肉埋我米饭底下,说“我不爱吃肥的”。 有次我半夜发烧,他背着我走了十里地去卫生院,凉鞋跑断了带,光着脚踩在石子路上,血珠子渗出来,混着露水在月光下亮晶晶的。我趴在他背上,听见他喘气像破风箱,却还哼着跑调的歌:“月亮走,我也走……” 你说这世上的缘分,是不是都藏在这些“本来要”和“偏偏没”里?他本来要收废铁,偏偏扎了胎;本来要路过,偏偏看见了那个啃发霉馒头的小孩;本来可以转身就走,偏偏蹲下来,递了块甜饼。 现在我二十多了,在城里开了家小修车铺,专门修三轮车。常有收废品的师傅来光顾,他们蹲在门口等修车时,我总会递瓶冰汽水,看他们仰头喝的样子,就想起那年夏天,蓝布衫后背的汗渍,和馒头皮上的绿霉——后来他总说“走对路哪能捡到宝”——这话我记了二十年。 前几天整理老屋,翻出他当年的记账本,第一页歪歪扭扭写着:“五月十六,收废品,遇一小娃,领回家。今日收入:-1个红糖饼。” 窗外的夕阳又落下来了,红得像刚出炉的糖糕。我想起他的三轮车,当年觉得像着火,现在才明白,那不是火,是光——是一个走错路的人,给另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点起的一盏灯。
我五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收废品的男人,他看我蹲在路边啃半块发霉的馒头,就把我领走了
嘉虹星星
2025-12-19 14:07:30
0
阅读: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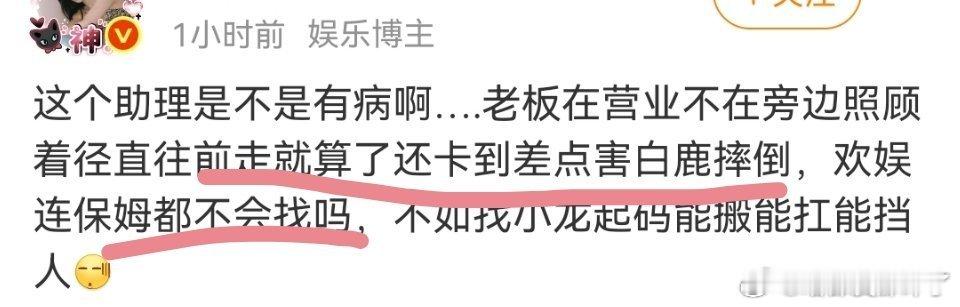




![珠江主入海口其实在珠海[呲牙笑][呲牙笑]](http://image.uczzd.cn/1176153588123736479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