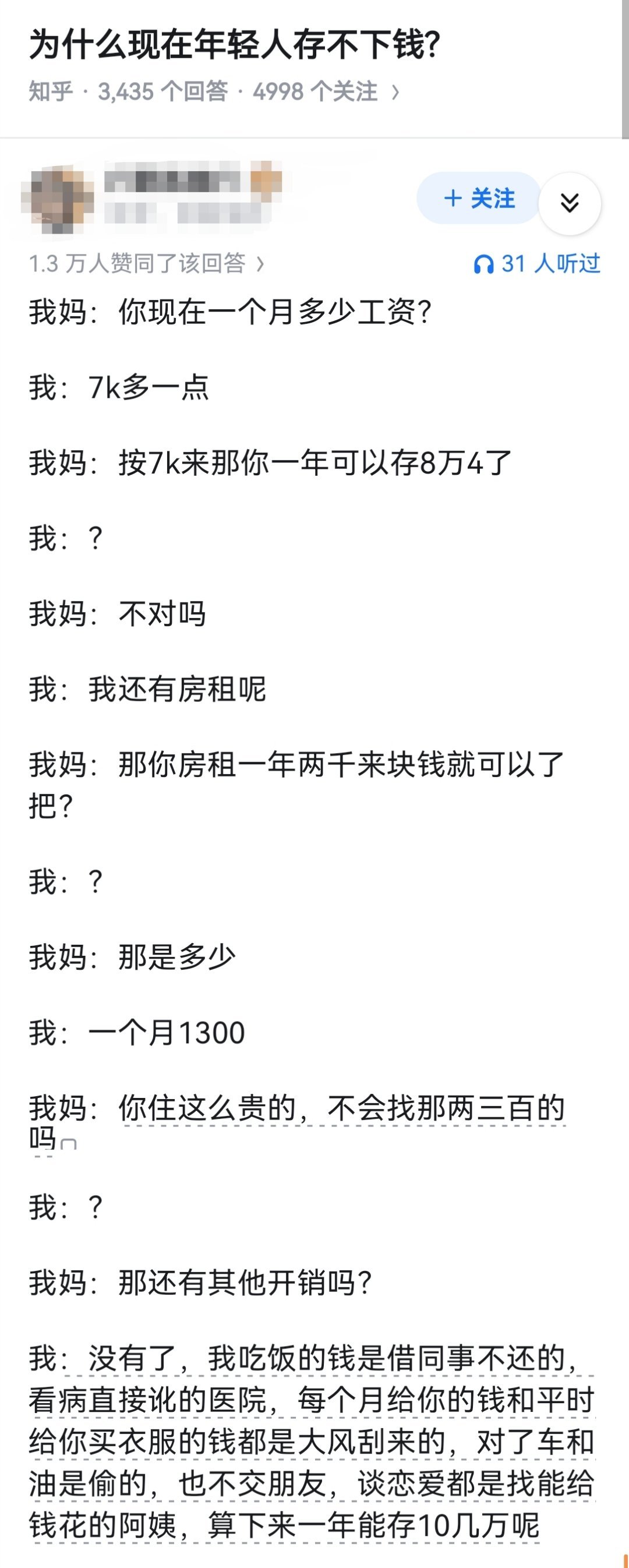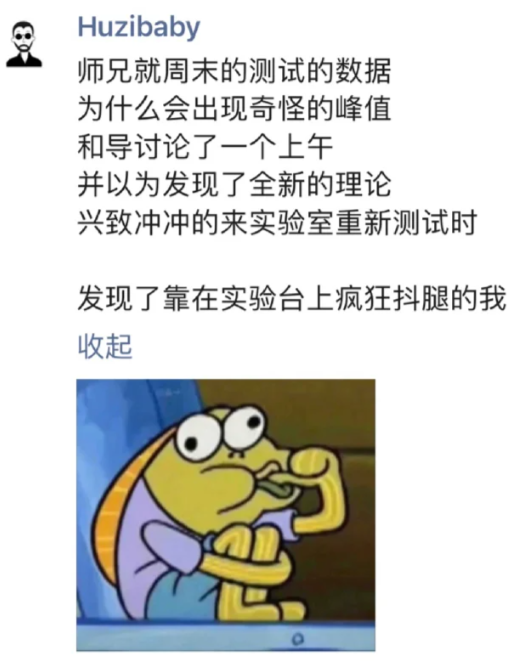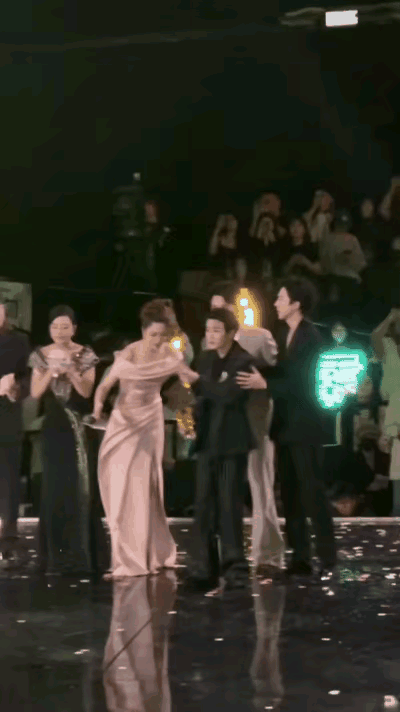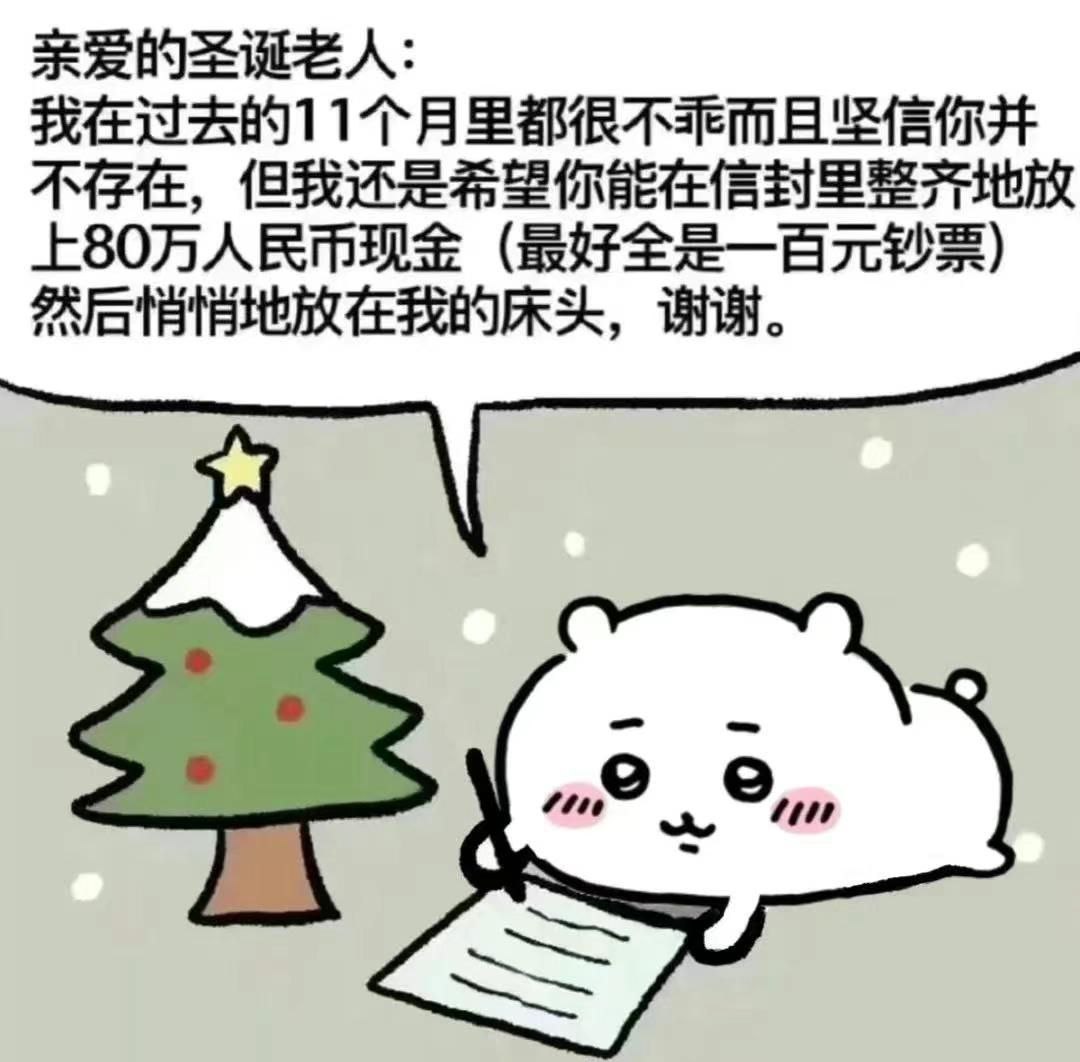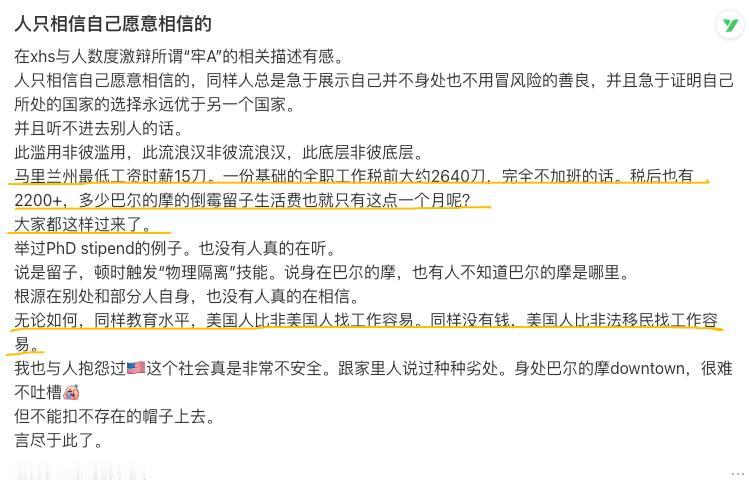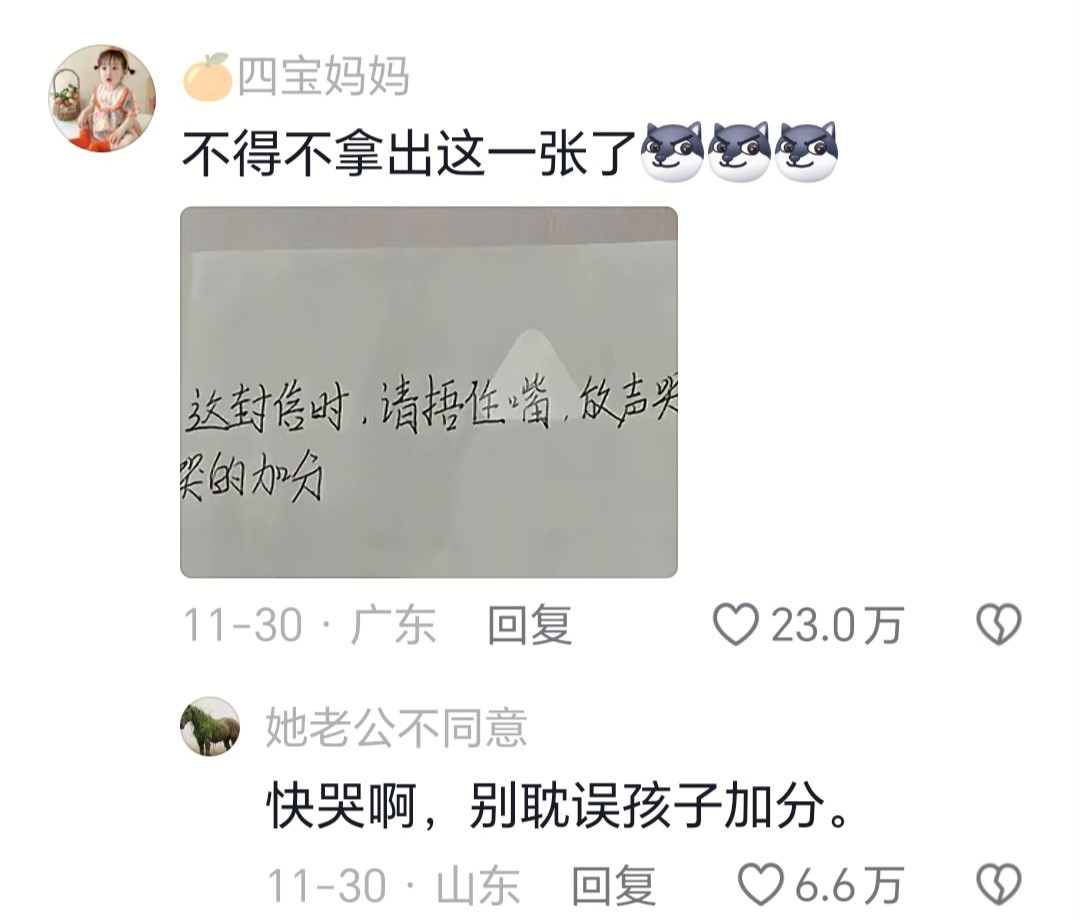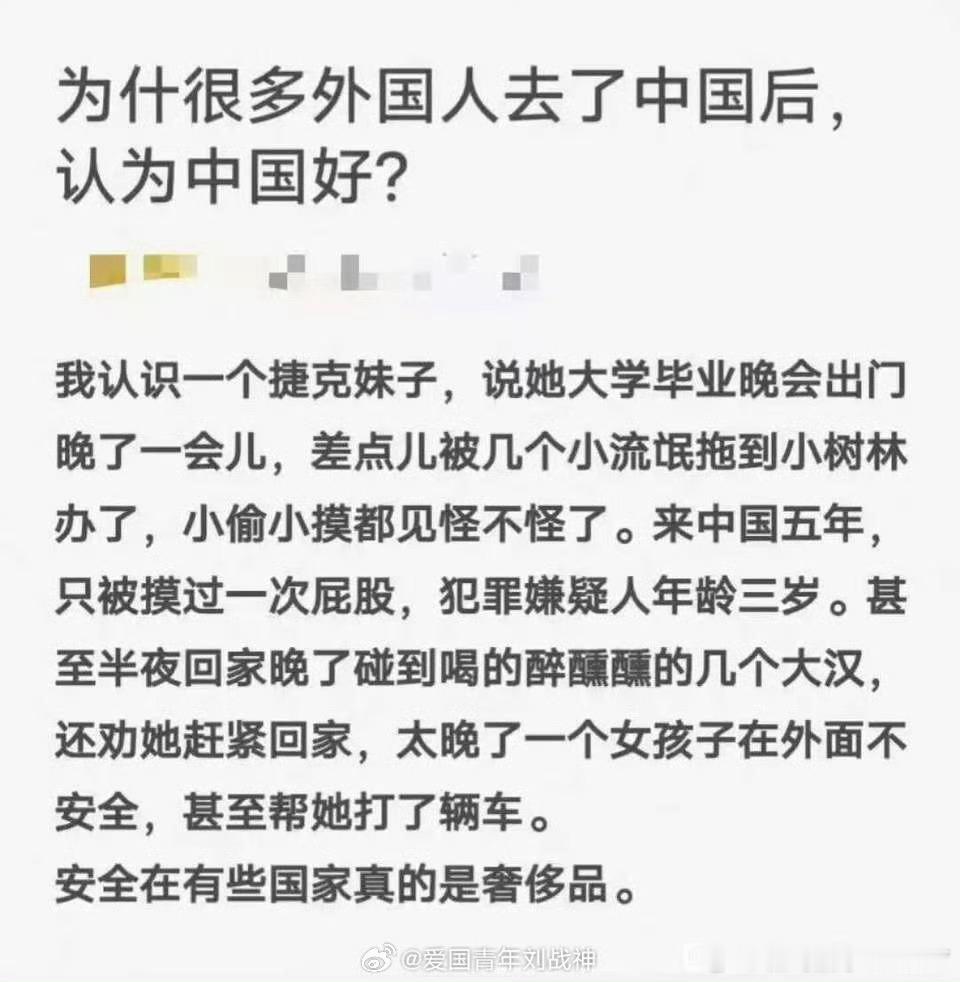为什么升米养恩,斗米养仇?因为大恩难报,是甩不开的负担。 我最近总想起初中校门口的老槐树,那年深秋,被高年级堵在巷子里时,学长张明从墙后走出来,校服拉链没拉好,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毛衣,他没说话,只是往我手里塞了瓶矿泉水,自己站在我身前,像堵不高却很稳的墙。 后来我总想找他,却连他考去哪个高中都不知道。去年同学聚会有人说他在邻市开修车行,我连夜查地址,手指悬在拨号键上两小时,最终还是关掉了页面。 不是不想见,是不敢。我总觉得该带点什么——至少是他当年那瓶水的千百倍价值?可他当时只是笑着说“下次再有人堵你,喊我”,眼里根本没把这当回事。 有人说这是懦弱,是不懂感恩。可小区里的李阿姨,当年受邻居资助读完大学,现在每年春节都提着水果去拜年,聊聊家常,倒也自然。为什么她能做到? 或许差别在“恩情的重量”由谁定义。李阿姨说,邻居从没提过“资助”,只说“当年看你读书辛苦,顺手帮一把”;而我们总在记忆里给恩人加滤镜——学长的背影被岁月拉得越来越长,老师批改作文时那句“这个比喻用得妙”,被我反复咀嚼成“她是我的伯乐”,最后连自己都信了:回报必须配得上这份“伯乐之恩”。 直到上周整理旧物,翻出初中日记本,某页歪歪扭扭写着:“今天张学长帮了我,明天我也要像他一样帮别人。”原来最初的想法那么简单,是后来的“必须涌泉相报”,把“帮别人”变成了“还不清的债”。 是我们把恩情看得太重,还是“回报”本身被赋予了太多附加条件?就像小时候收到压岁钱,父母总要叮嘱“记得说谢谢,长大了要孝顺”,那份纯粹的喜悦里,不知不觉掺进了“以后要还”的暗示。 短期看,这份负担让我们逃避见面;但往深了想,它也在提醒:恩情本该是流动的活水,不是要存起来发酵成酒的——当年那瓶水的温度,比十年后任何昂贵的礼物都实在。 现在路过老槐树,我会买瓶矿泉水放在树下,像当年他塞给我那样。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回报:把那份“升米之恩”,换成递给下一个人的“升米”,让负担变成接力。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存不下钱?
【1评论】【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