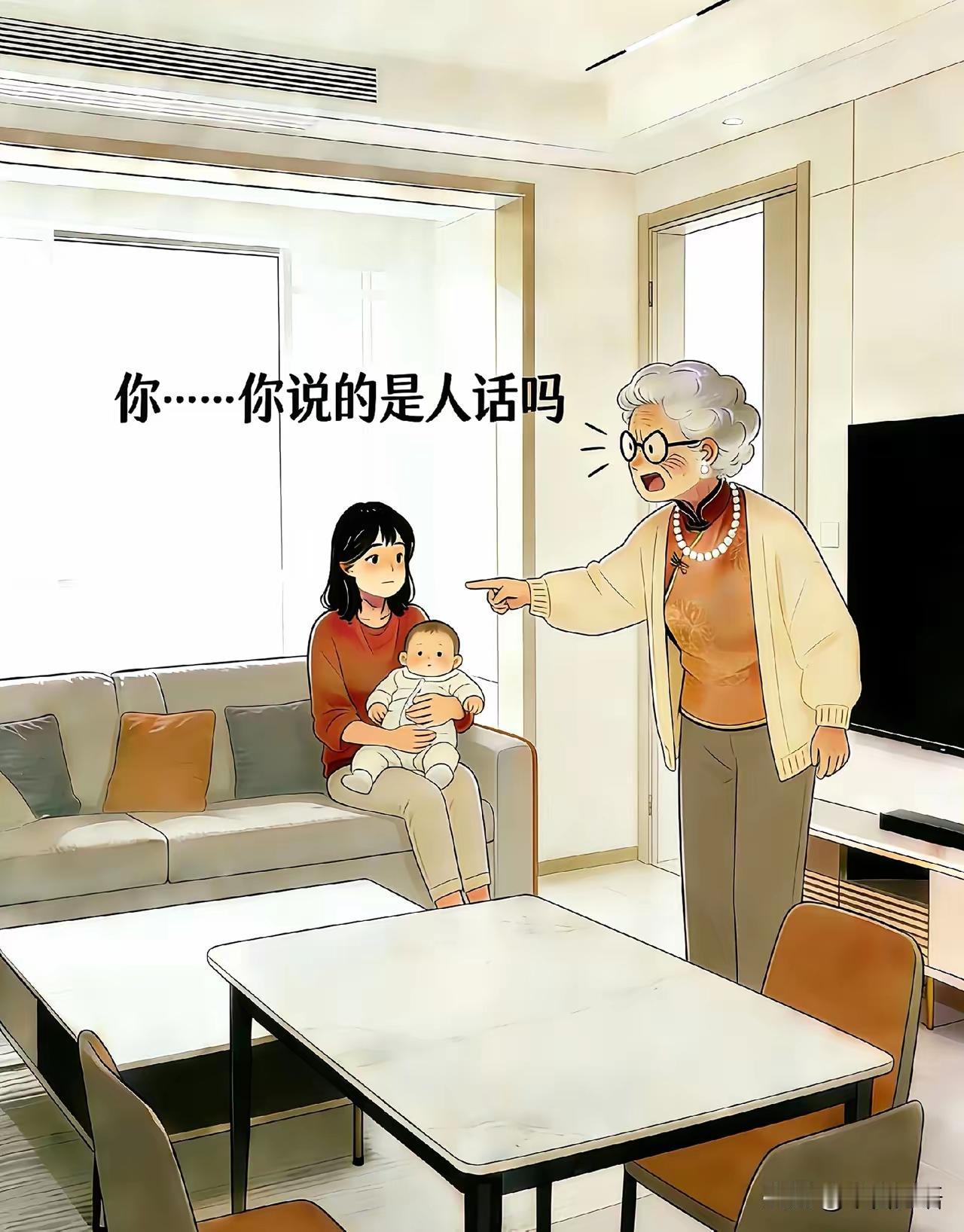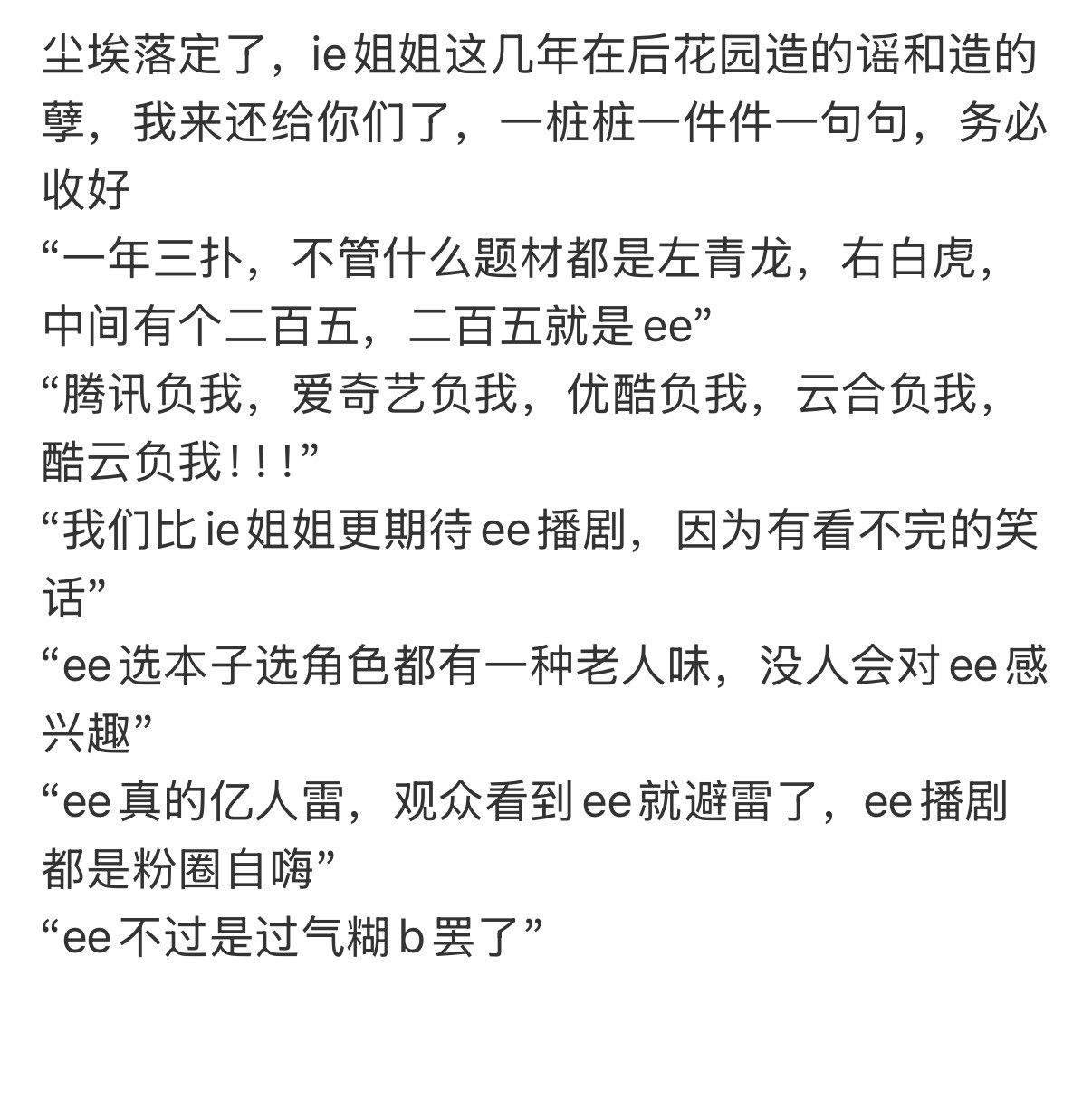我是一个女人,我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最小的。怀老三那年,村里的人见了我就说“这下好了,总算盼到儿子了”。婆婆每天给我炖鸡汤,说“多补补,给咱家留个根”。我摸着肚子里的小生命,心里却想着大女儿掉在地上的铅笔头,二女儿总说“妈妈,我也想上学”。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最小的那个。 怀老三那年,村里的人见了我就凑上来笑:“这下好了,总算盼到儿子了。” 婆婆每天雷打不动炖鸡汤,砂锅里的油花浮在面上,她端过来时总要摸一把我的肚子:“多补补,给咱家留个根。” 我摸着肚子里轻轻踢腾的小生命,鼻尖萦绕着鸡汤的香,眼前却总晃着大女儿早上掉在地上的铅笔头——那是她用了半学期的铅笔,断了尖,她蹲在地上捡,马尾辫扫过我的裤腿,我当时正忙着接婆婆的汤碗,只随口说了句“快起来”。 二女儿昨晚钻被窝时,小手攥着我的衣角:“妈妈,姐姐说学校里有图画课,我也想上学,我会乖乖坐好,不乱跑。”我那会儿正被孕吐搅得没力气,拍了拍她的背:“乖,等弟弟生下来再说。” 村里人说“盼到儿子”的时候,真的觉得我该高兴吗? 可她们不知道,大女儿刚会走路时,我牵着她的小手在院子里学步,她跌跌撞撞扑进我怀里,我抱着她转圈圈,觉得全世界的光都在她眼睛里;二女儿第一次叫“妈妈”,我抱着她亲了满脸口水,夜里偷偷给她织小袜子,针脚歪歪扭扭也笑得睡不着——她们也是我拼了命生下来的宝贝啊。 婆婆说“留根”的时候,大概觉得女儿们就像开过的花,谢了就谢了,只有儿子才是能结果的树吧? 可我总想起大女儿掉在地上的铅笔头,她捡起来后用牙齿咬着削,木屑掉了一嘴;想起二女儿扒着学校的栅栏往里看,小脑袋跟着操场上跑跳的孩子转,手指把栅栏栏杆抠出了白印子——这些画面,比鸡汤的香味更让我心里发紧。 所谓“盼到儿子”,或许只是村里人按老规矩说的客套话;所谓“留根”,也只是婆婆那辈人刻在骨子里的念头;可我是妈妈啊,我的心怎么能真的跟着这些话,把女儿们归成“不重要”的那部分? 那天炖鸡汤的火有点大,汤溢出来溅在灶台上,婆婆慌忙去擦,我却突然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大女儿正蹲在墙角用断铅笔头在地上画小人,二女儿趴在她旁边看,两个人头挨着头,影子在地上叠成小小的一团。 我走过去蹲下来,捡起地上的断铅笔头,大女儿抬头看我,眼里有点怯怯的:“妈妈,我没弄脏地。” “妈妈知道,”我把铅笔头揣进兜里,摸了摸她的头,又转向二女儿,“你不是想上学吗?等妈妈生完弟弟,咱们就去问老师,什么时候能报名,好不好?” 二女儿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落了星星:“真的吗?” “真的,”我把两个女儿搂进怀里,闻着她们头发上晒过太阳的味道,“妈妈记得呢,都记得。” 后来儿子出生了,婆婆抱着小孙子笑得合不拢嘴,村里人又来说“这下圆满了”。 可我知道,真正的圆满不是“盼到儿子”,是大女儿不再用断铅笔头画画,二女儿背上书包走进教室时,眼睛里的光比星星还亮;是每个孩子的小愿望,都被妈妈稳稳地捧在手心。 现在我的兜里总装着削笔刀,大女儿的铅笔再也不会断到只能用牙啃;二女儿每天放学回来,都会把图画课的作业举到我面前,奶声奶气地讲画里的故事。 地上的铅笔头早就不见了,但我总想起那个画面——那天的阳光很好,两个女儿的影子叠在一起,而我终于明白,母亲的心从来不该分轻重,每个孩子,都是上天赐给我最完整的礼物。
我是一个女人,我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最小的。怀老三那年
凯语乐天派
2025-12-27 10:31:28
0
阅读: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