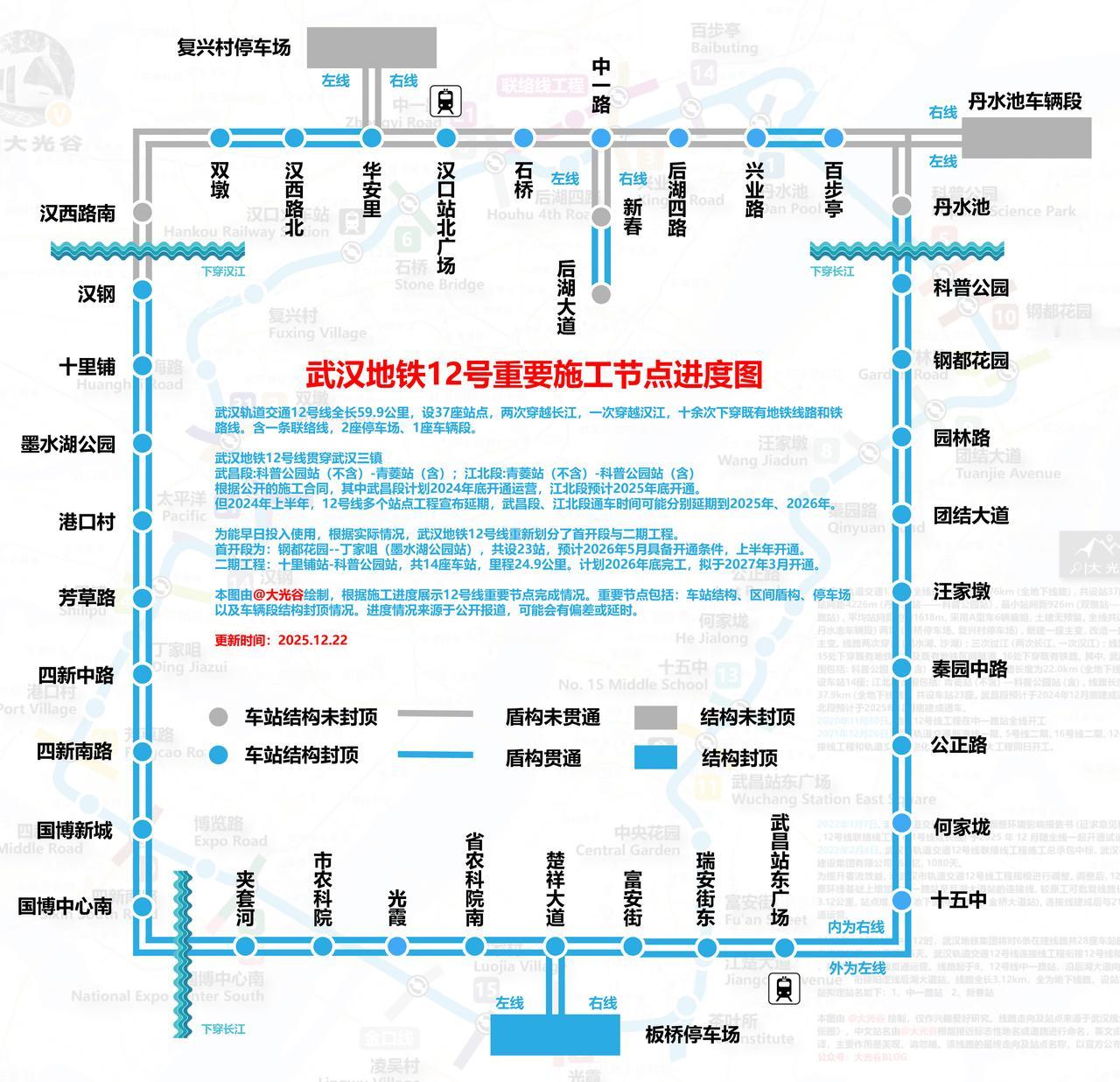我姐夫就是个垃圾。在武汉开家螺丝工厂,那几年行情好,赚到钱了,开始飘了,看不起我这个小舅子,经常不待见我,买车买房高调的很。第一次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是我妈六十大寿那年。一家人在酒店订了包厢,我提前半小时到,刚坐下就看见姐夫开着新买的奔驰E级停在门口,西装革履地走过来,手里还拎着个名牌包。我赶紧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却只是瞥了我一眼,淡淡地“嗯”了一声,就径直走进了包厢。 我和姐夫,以前不算多亲,但也没红过脸。 他在武汉开螺丝厂那几年,我常去给他搭把手搬货,他总拍着我肩膀说“等哥发了,给你也整辆代步车”,油污蹭在他袖口上,笑得一脸憨实。 后来行情真的好,厂里的螺丝一车车往外卖,他的钱包鼓了,身上的烟火气却少了——先是换了最新款手机,接着在光谷买了房,最后连说话的调门都高了八度,话里话外总带着点“你们不懂”的轻慢。 我妈六十大寿那天,一家人在武昌那家老酒店订了包厢,我特意提前半小时到,想帮着摆摆碗筷、试试音响。 刚在靠窗的位置坐下,就听见楼下传来引擎声,抬头一看,是辆崭新的奔驰E级,银灰色的车身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眼晕,轮胎碾过地面的声音都比别家车响脆些。 车门打开,姐夫下来了,西装熨得笔挺,领口别着个精致的袖扣,手里拎着个印着字母的包,以前总沾着铁屑的指甲缝,现在干干净净的,还泛着护手霜的光。 我赶紧站起来,笑着迎上去:“姐夫,你可算来了,妈刚还念叨你呢,说你忙完了没。” 他脚步没停,眼睛从我的旧夹克上扫过去,像是在看酒店门口的石狮子,然后从鼻子里“嗯”了一声,径直往包厢里走,那包带子在我眼前晃了晃,带着股淡淡的古龙水味,盖过了酒店大堂飘来的桂花香气。 我僵在原地,手还举在半空,身后的服务员端着茶水走过,瓷杯碰撞的声音脆生生的,倒显得我这声招呼格外多余。 那天的寿宴,满桌子的菜热气腾腾,清蒸武昌鱼、排骨藕汤,都是妈爱吃的,可我没什么胃口——他坐在主位,和亲戚们聊生意,说哪个客户又订了多少万的货,说城里的学区房涨了多少,偶尔看向我,也只是夹一筷子菜,随口问“你那工作还那样?一个月够花吗”,语气里的打量,像在评估一件滞销的库存。 我没接话,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心里像压了块浸了水的棉花,沉得喘不过气:以前他骑二手面包车时,车窗摇不上去,冬天漏风,我们缩在车里啃面包,他说“等以后有钱了,一定买辆带暖气的,让你姐不受罪”,那时的风是冷的,可他眼里的光,比暖气片还热乎;怎么现在车有暖气了,人却冷了呢? 是钱真的能把人变了,还是他本来就这样,只是以前没机会显露?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他厂里接了个大订单,天天和供应商扯皮,那天早上刚和人吵完架,或许真的累得没心思应付这些人情往来? 可就算再累,对家里人,总该有句像样的问候吧? 事实是,从那以后,他对我越来越淡:我结婚时他包了个红包,数字比我堂哥还少;我爸生病住院,他只让姐姐带了束花来,人都没露面。 推断起来,大概是他觉得自己已经站在“成功者”的队伍里,而我还在原地,我们之间的“价值交换”不对等了,自然没必要再花心思维持那份亲近。 影响呢?影响就是后来过年聚会,我都尽量坐在离他最远的位置,他说话我就低头玩手机,他敬酒我就抿一小口,姐姐看在眼里,私下跟我说“你姐夫就是性子直,你别往心里去”,可她眼里的无奈,比我心里的委屈还清楚。 短期结果?那天寿宴散场,我帮着收拾东西,看见他落在椅子上的西装外套,想递给他,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万一他觉得我想攀附,岂不是更丢人? 长期影响?现在我们一年也说不上十句话,上次在医院碰到,他陪着客户看病,我抱着孩子从电梯出来,他看了我一眼,像是没认出来,擦肩而过时,我听见他对客户笑着说“那都是小生意,不值一提”。 当下可操作的提示是什么呢?或许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一些人,像坐公交车,陪你走了几站,到站了,就该下车了——只是下车前,能不能好好说声再见? 走出酒店时,天已经黑了,那辆奔驰E级还停在路边,车窗贴着深色的膜,看不清里面的人。 我想起以前他开二手面包车时,车斗里堆着螺丝箱,我们挤在驾驶座,他哼着跑调的歌,说“等赚够了钱,就把厂交给别人管,带你姐去自驾游”,那时车是破的,路是颠的,可心里是暖的;现在他的车宽敞又平稳,我却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比车窗上的膜还厚。 你说,钱到底是让人活得更体面,还是让人把心裹得更严实了?
武汉这姑娘脾气真是火辣,一句你啥都没有,凭啥嫁给你?瞬间戳穿了她重视物质条件
【11评论】【5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