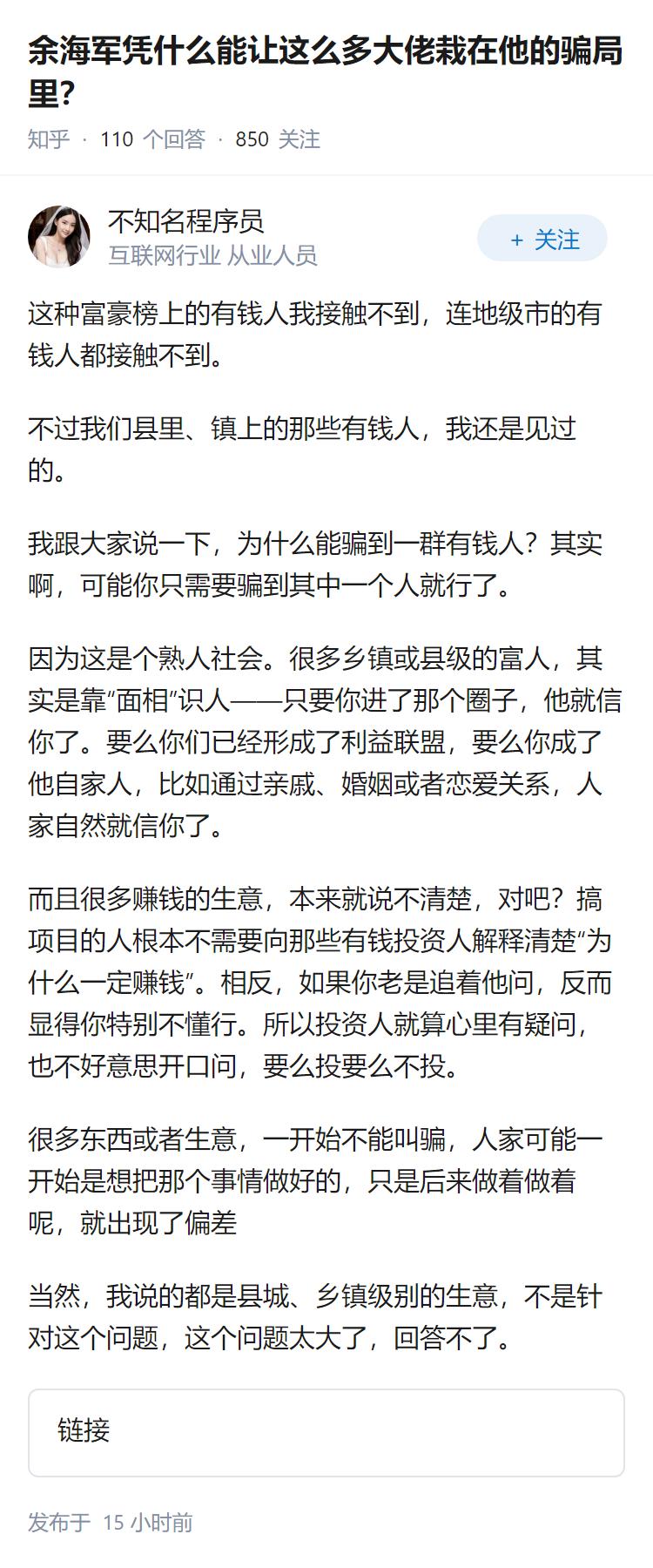我有个战友,在部队是司务长,正排级转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进了县人民法院,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当上了法官。 消息传来,我们这帮战友都傻眼了。老陈?那个在炊事班围着锅台转、算大白菜账比谁都精的老陈?他能敲法槌?聚会时,电话里恭喜的话都带着股子酸味儿。他只憨厚地笑:“去了再说,去了再说。” 他报到后,我们就很少见他了。有次我去县城办事,顺道去法院找他。他办公室在走廊尽头,老旧的吊扇吱呀呀地转着。他正埋头看卷宗,桌上堆得山高,旁边还摊着本翻烂了的《民法典》。见我来了,他赶紧起身,手忙脚乱地找茶叶,暖壶却是空的。 “忙,太忙了。”他搓着手,有点不好意思。我瞥见他笔记本上,字写得跟小学生一样,一笔一划,但密密麻麻。聊了没几句,他书记员探头进来,说有个老太太在调解室,非要见陈法官。“你看……”他冲我苦笑。我摆摆手,让他赶紧去。 我没走,隔着调解室的玻璃窗看了一眼。老太太头发花白,正在抹眼泪,手里攥着一把皱巴巴的欠条。老陈没坐法官席,拖了把椅子坐到老太太对面,弓着背,听她絮絮叨叨地说,时不时在本子上记两笔。他说话声音不高,我也听不清,只看见他倒了杯热水递过去。过了约莫半小时,老太太站起身,朝他鞠了一躬,虽然还是擦着眼睛,但神色松快了些。 晚上,我拉他出来吃碗面。面馆吵得很,他呼噜呼噜吃得很快。“今天那老太太怎么回事?”我问。他放下碗,叹了口气:“儿子工伤没了,包工头赖抚恤金。法律条文她听不懂,就认死理。我能做的,就是听她说完,再告诉她,法院管这个,我管这个。” “难吗?”我看着他眼里的血丝。他笑了笑:“比配营养餐难。但道理差不多,都得对得住人。”他摸出烟,想了想又塞回去,“下个月要开庭审那个包工头,证据链得捋顺,一点都不能错。” 结账时,他抢着付了钱。走出面馆,县城华灯初上。他挺了挺那总是微微弓着的背,身影汇入人流。我想,法袍下面,或许还是那身洗白了的军装脊梁。
076两栖攻击舰飞行甲板上停放的粽子机,这架飞机被包裹的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见。
【4评论】【3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