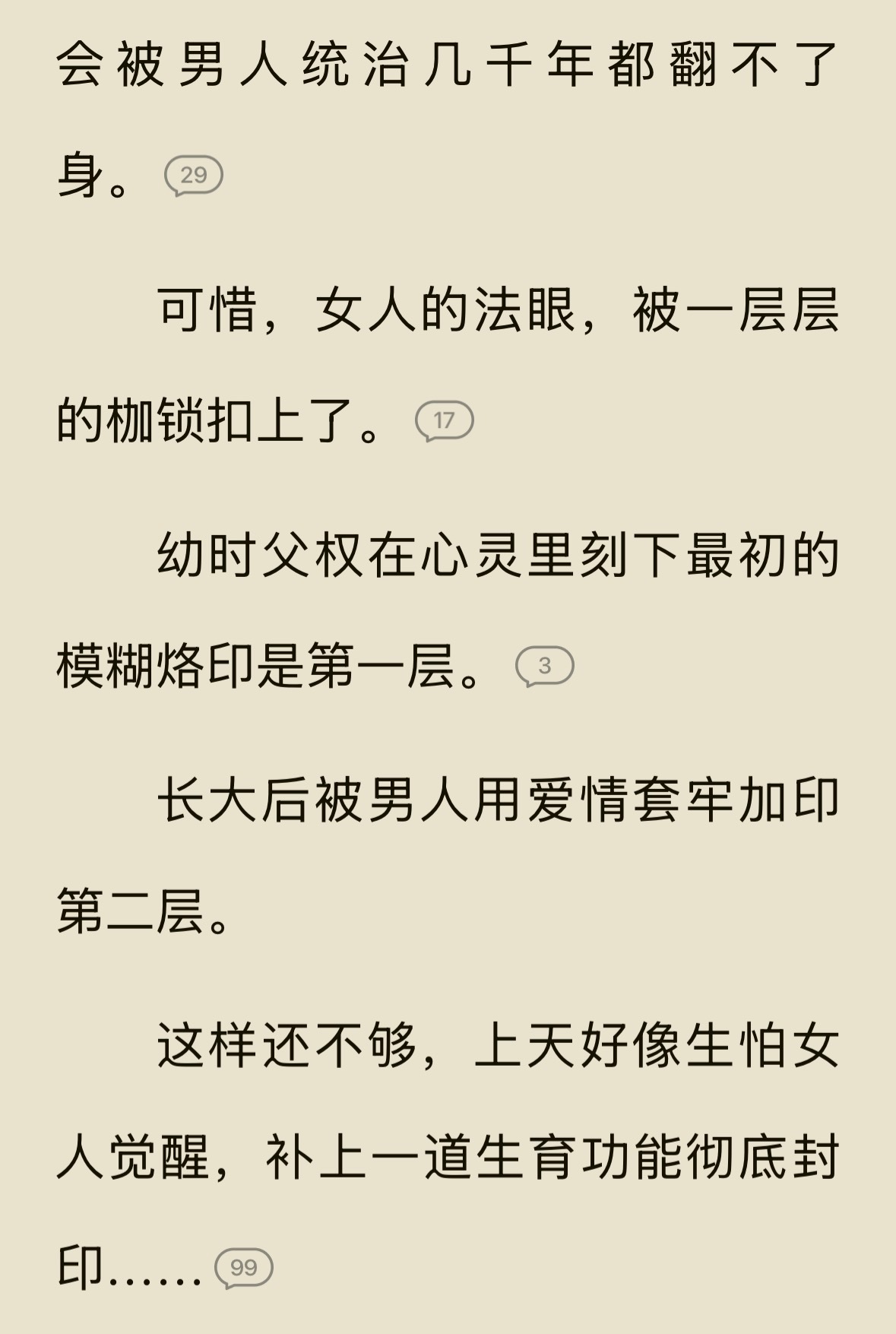我下乡当知青时,有一次跟生产队的马车往粮库送公粮,在粮库食堂吃一顿免费伙食,不限量的吃。 那天我们凌晨就出发了。我和老陈、建国挤在一辆马车上,身子底下是硬邦邦的麻袋。路不好走,颠得人骨头疼。天蒙蒙亮时,路过一片河滩,驾辕的老青骡子不知怎么,一脚踩进个泥坑,车子猛地一歪,最边上两个麻袋滑了下去,摔破了口子,金黄的麦粒撒了一地。 我们都吓傻了。这可不是小事。队长脸黑得像锅底,蹲在地上,用手一把一把地把麦子往破口里捧。我们也赶紧跳下车,用手捧,用帽子装。可河滩上碎石土块多,混进去的杂质怎么也拣不干净。 赶到粮库时,果然验粮员一查就皱了眉。“这粮不行,有土,得筛干净再收。”队长低声下气地求情,说我们路远,能不能通融。验粮员是个黑脸汉子,挥挥手说,粮库有规矩,不行就是不行。他指了指院子角落一个旧风车,“自己去弄,弄干净了再过秤。” 午饭时间早就过了,食堂那边飘来的香味一阵阵往鼻子里钻。我们仨肚子叫得像打鼓,但谁也没提吃饭的事。队长闷头抽完一袋烟,说:“干吧。”四个人,就守着那个破风车,一锹一锹地把麦子扬起来,让风吹走杂质。初秋的太阳还挺毒,晒得人头皮发麻,汗水流进眼睛,刺得生疼。 弄了快俩钟头,手掌磨得火辣辣的,才总算把两袋粮弄干净。重新过秤、入库,所有手续办完,日头已经偏西了。粮库大院空荡荡的,送粮的车队都走光了。 我们拖着步子往食堂走,心里都凉了半截,估计啥也吃不上了。走到食堂门口,那个黑脸验粮员正蹲在门槛上抽烟。看见我们,他站起身,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食堂。我们愣在门口。 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个大簸箕出来,里面放着十来个大白馒头,还有一大碗咸菜。“灶火封了,就剩这些,”他把东西往我们手里一塞,“凑合吃吧。”说完,又蹲回去抽烟了。 我们靠着马车轮子,分着吃那些凉透的馒头。馒头很瓷实,嚼在嘴里有淡淡的甜味。咸菜疙瘩齁咸,但就着吃,特别香。谁也没说话,就听着咔嚓咔嚓的咀嚼声。 老陈吃到一半,忽然停了一下,小声说:“他也没吃呢。”我们抬头,看见那验粮员还蹲在那儿,望着远处。队长拿起两个馒头走过去,放在他旁边的石头上。验粮员看了一眼,没动,也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月亮已经升起来了。马车慢悠悠地晃着,我们都累了,靠着麻袋打盹。风凉丝丝的,带着庄稼成熟的香气。我怀里揣着省下来的半个馒头,硬硬的,贴着胸口有点硌,但很踏实。
我下乡当知青时,有一次跟生产队的马车往粮库送公粮,在粮库食堂吃一顿免费伙食,不限
小杰水滴
2026-01-29 23:32:30
0
阅读:56